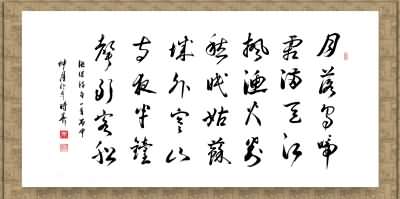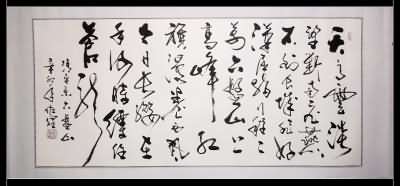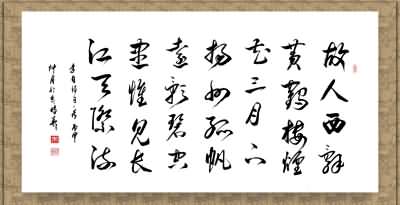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為銘之矣,而元實復請記焉。
夫裕者,寬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盈丈,高不逾仞,庭不容拱把之木,逕不通一馬之足。櫛櫛密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
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猗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
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多於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游,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卑,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
甲午之歲,余闢地於越,主王氏,知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
會稽人王元實在他的居所一旁新建了一座小書齋,為它取名叫裕軒。我已經為他的這座小書齋題了名,而王元實又請(我)為此作記。
所謂的裕,說的是寬廣的意思。如今王元實的這座小書齋,大小不滿一丈見方,高度不超過一仞(七尺),院子(小得)不能容下兩手合圍那麼粗的一棵樹,小路(小得)不能通過一匹馬的腳。院子裡顯得很是稠密,門戶狹窄逼仄,看不到一絲空隙,卻稱之為「裕」,可以嗎?一般人所認為的豐裕在於看得見的物,而王元實先生所認為的「豐裕」(卻是)在心裡;一般人都以我們擁有充足的物質為豐裕、充裕,王元實先生(卻只知道自己內心的)豐裕、充裕而不知道看得見的物質的豐裕不豐裕。於是我們的內心豐裕了而物質從而也就豐裕了,這大概就是(王元實先生)為這座小書齋命名為「裕」的原因吧?
一般人的憂慮憂愁都集中在感情情緒上,喜好快樂也都受到內心的牽動。我要想物質生活富裕,當年西晉石崇與王愷斗富時炫耀的珊瑚樹也不算多,西蜀之地盛產銅礦的銅山也不算富饒,陶朱公和猗頓積聚的財富也不算豐厚;我要想地位尊貴,通侯(徹侯)和州郡的長官也不算尊貴,士大夫所乘用的大車和顯貴者所乘的駕四匹馬的高車也不算榮耀,萬鐘的豐厚俸祿和列五鼎而食的奢侈豪華的生活也不算滿足;我要想享受娛樂,吃飯時面前的食物佔據了一丈見方的地方也不算奢侈,歌舞華美也不算過分,到處狩獵也不算廣泛無度,珍奇的鳥類和供玩賞的珍品充滿供人遊憩歇宿的亭台館舍也不算奢侈華麗。那麼(我)一定會竭盡全力來求取這些,(如果)有什麼得不到,就會食不甘味、寢臥難安。如此一來,即使是遊遍廣大無邊的原野,登上高大廣闊的山丘,(我也)會覺得無處容身,又怎麼能稱之為「豐裕」呢?
而王元實先生卻不是這樣的,吃一盂飯就飽了,喝酒就醉了,不要求太多的飲食,而我內心就覺得很豐裕了;夏天鋪一床細葛布的蓆子就覺得很涼爽,冬天蓋一件皮衣就覺得很暖和,不要求太多的衣服,而我內心就覺得很豐裕了;朗誦一下我喜歡的詩歌,朗讀一下我喜歡的書籍,心情舒適的時候就外出遊玩,玩夠了就停下來休息,累了就躺下來睡覺,不要求太多的遊樂和珍物玩賞,而我內心就覺得很豐裕了;腳步不踏入訴訟的廳堂,耳朵不聽取市集上的閒言,眼睛不沉溺於(美女)嬌美妖冶的容顏,嘴中不談論國家政事的是非,也不要求稱為道德高尚的人,而我內心就覺得很豐裕了。一張床很小,(但是)除了能容身之外我不再需要別的;一間房子很小,除了能遮蔽風雨之外不是我擔憂的事;家裡的僕役愚鈍,子侄後輩們癡傻,除了能夠供差遣使喚之外不是我所要求的,既然這樣,那麼怎麼不能夠感到「豐裕」呢?
甲午年,我為躲避禍患遷居到越地,主人王氏,瞭解王元實先生得為人,與他交往而關係友善,於是我為此寫下了這篇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