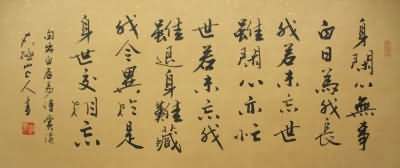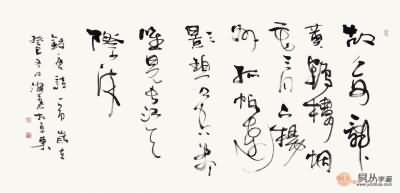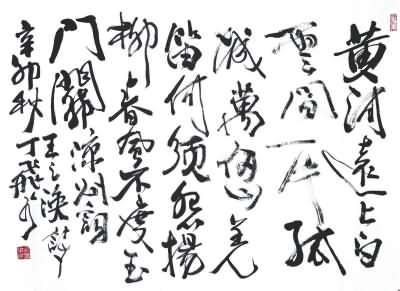魏濟北郡從事椽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夕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覺而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色,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清白琉璃,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蓋宿時感運,宜為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為損。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為君生子,亦無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為夫婦。贈詩一篇曰:「飄搖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舉。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為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楊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經七八年,父母為超取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也。每超當有行來(來原作永,據明抄本改),智瓊已嚴駕於門。百里不移兩時,千里不過半日。超後為濟北王門下掾,文欽作亂,魏明帝東征,諸王見移於鄴宮,宮屬亦隨監國西徙。鄴下狹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獨臥,智瓊常得往來。同室之人,頗疑非常。智瓊止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之氣,達於室宇,遂為伴吏所疑。後超嘗使至京師,空手入市。智瓊給其五匣弱緋、五端絪貯。采色光澤,非鄴市所有。同房吏問意狀,超性疏辭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監國,委曲問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責也。後夕歸,玉女己求去,曰:「我神仙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啗,發簏,取織成裙衫兩襠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零溜漓,肅然升車,去若飛流。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積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智瓊。驅馳前至,視之果是,遂披帷相見,悲喜交至,授綏同乘至洛,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月往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來,來輒經宿而去。張茂先為之賦《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如弦氏之歸,則近信而有徵者。」甘露中,河濟間往來京師者,頗說其事,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東上,論者洋洋,異人同辭,猶以流俗小人,好傳浮偽之事,直謂訛謠,未遑考核。會見濟北劉長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親見義起,受其所言,讀其文章,見其衣服贈遺之物,自非義起凡下陋才所能構合也。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云:「當神女之來,鹹聞香薰之氣、言語之聲。」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又人見義起強甚,雨行大澤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燕寢處,縱情兼欲,豈不異哉!(出《集仙錄》)
【譯文】
魏時,濟北郡從事椽弦超,字義起,在嘉平年間有一天晚上獨宿,夢見有個神女來侍從他。神女自稱是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年失去父母。上帝因為她孤苦無依而哀憐她,令她下界嫁人。弦超正當做這個夢的時候,精神爽快,感覺靈悟,覺得神女的姿容不是平常人所能有的那麼美,醒來的時候他就懷著敬意想念她。一連三四個晚上都是如此。有一天,智瓊真真切切地來了,駕著上有帷蓋四周有帷幕的車子,隨從八個婢女。穿著羅綺製作的衣服,容顏姿色象飛仙的樣子。她自己說七十歲了,可是看起來就像十五六歲。車上有盛放酒壺的盒子,潔白琉璃,有各種吃的喝的等奇異食品,還有餐具和美酒。來到以後,她就與弦超共飲共食。她對弦超說:「我是天上的玉女,被遣下嫁,所以來依從您。原因是前世時感運相通,應該做夫婦。我對您雖然不能有益,也不會造成損害。但卻能使您經常能夠駕輕車乘肥馬,飲食經常可以得到遠方的風味和奇異的食品,絲綢錦緞可以得到充足的使用而不缺乏。然而我是神人,不能給您生孩子,也沒有妒忌的性情,不妨害您的婚姻之事。」於是,他們結為夫婦。智瓊贈給弦超一首詩:「飄遙浮勃蓬,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這是那首詩的大意。全文二百多字,不能全部列舉。智瓊又著闡發《易經》的書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為屬。所以從其文意來看,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卜吉凶,如同楊雄的《太玄經》和薛氏的《中經》。弦超對它的意旨都能通曉,運用它占卜。經過七八年。弦超的父親給弦超娶妻之後,他們就分日宴樂,分夕而共寢。智瓊夜間來早晨去,迅捷如飛,只有弦超能看見她,別人都看不見她。每當弦超要遠行時,智瓊就已經把車馬行裝安排得整整齊齊等在門前,走百里路不超過兩個時辰,走千里路不超過半天。弦超後來做濟北王的門下掾,那時文欽作亂,魏明帝東征,諸王被遷移到鄴宮,各王宮的屬吏也隨著監國的王爺西遷。鄴下狹窄,四個吏員同位一間屋子。弦超獨臥時,智瓊照常能夠往來,同室的人都懷疑弦超不正常。智瓊只能把自己的身形隱匿起來,但是不能把聲音也藏起來、而且芳香的氣味,彌滿屋室,終於被同室相伴的吏員所懷疑。後來弦超曾經被派到京師去,他空手進入集市,智瓊給他五匣弱紅顏料、五塊做褥子的麻布,而且彩色光澤,都不是鄴城集市所有的。同房吏盤問他這是怎麼回事,弦超性格疏朗,不善言辭,就詳詳細細地向他們說了。同室小吏把這些情況向監國王爺報告了,監國向他訊問了事情的底細和原委,也恐怕天下有這種妖幻,就沒有責怪他。後來,弦超晚上回來,玉女自己請求離去,她說:「我是神仙,雖然與您結交,不願讓別人知道。而您的性格粗而不細,我今天底細已經暴露,不能再與您通情接觸了。多年交往,結下情誼,恩義不輕,一旦分別,哪能不悲傷遺憾?但情勢如此,不得不這樣啊,我們各自努力吧!」智瓊喚侍御的人擺下酒飯,又打開柳條箱子,拿出織成的裙衫和兩條褲子留給弦超。又贈詩一首,握著弦超的手臂告辭,眼淚流淌下來,然後表情嚴肅地登上車,像飛逝的流水一般離去了。弦超多少天來憂傷感念,幾乎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智瓊去後五年,弦超奉郡裡的差使到洛陽去,走到濟北魚山下,在小路上向西走,遠遠地望見曲洛道旁有一輛馬車,認出是智瓊,他就打馬向前跑。到跟前一看果然是智瓊,於是就掀起帷布相見,兩個人悲喜交加,智瓊讓他上車拉住繩索,同車到洛陽。他們又重修舊好,到太康年間還在。但是並不天天往來,只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和每月初一、十五見面。智瓊每次到來,往往經宿而還。張茂先為她寫了《神女賦》,其序文說:「世上談論神仙的人很多,然而沒有人驗證它,如弦超之妻的到來,就是近於事實而有驗證的例子。甘露年間,河濟一帶往來京城的人都傳說這件事,聽到的人常常認為智瓊是鬼魅一類的妖孽。等到遊歷東方,談論的人滔滔不絕,不同的人說的卻都一樣。還有人認為流俗小人好傳虛浮偽詐之事,逕直說是訛傳的謠言,未及考核。及會見濟北劉長史,他這個人是個明察有信之士,他親自見過弦超,聽弦超親口說過,讀過智瓊的文章,見過那些衣服等智瓊贈送的物件,自然不是弦超這種平凡低下、才疏學淺的人所能編造的。又推究查問左右知道這件事的人,他們說當神女來時,全都聞到了薰香的氣味,聽到了言語之聲,這就明顯地證明不是弦超因為夢想而造成的淫惑了。又有人見到弦超很強壯,在雨中行經大澤而不沾濕,就更加覺得奇怪。鬼魅接近人,無不使人身體羸弱生病受損而消瘦。如今弦超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宴同寢相處,縱情恣欲,難道不奇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