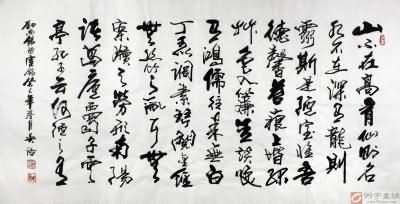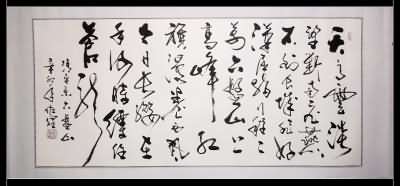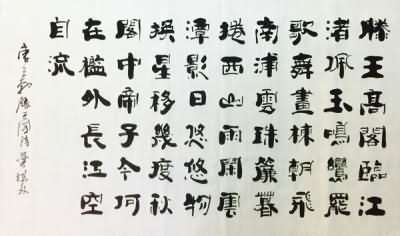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昆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歡,蓋莫不慼然於侯之去者。
噫!人之相與,歷歲月之久未必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
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扑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有不能昧者,而見於里巷之歌謠也。蓋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使之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於今而獨惡耶?
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傯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為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攜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鉤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諜而屠刳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於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沾溉於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期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雲。
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選自《震川先生集》卷十一,有刪改)
張侯,由尚書秋官郎,改任蘇州判。正逢其轄縣昆山縣令空缺,(張牧)前來代理此職。未到一個月,新縣令到任。我們這幫玩友,聚會在玉山南面,特邀張侯共盡一日之歡,沒有人不為張牧的離去感到傷感的。
啊!人之間的交往,有的經歷過很長的歲月,卻未必彼此友愛;不只不能互相友愛,有的甚至厭煩了長時間的往來,而避之不及。像張侯這樣不瞧不起我們,且我們也因此熱愛他,可以說是有情了。官吏們的來歷,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沒有戒親戒友的老關係。一旦因皇帝的任命,忽然像這樣聚到一起,難道是法度的威力所能強求(友愛)的?也只有憑借情感才能相知相愛罷了。現在有些人自以為 能決定自己管轄的百里地盤內的人的生死,認為依靠法度威力就能做得到,對別人漠不關心,卻放縱自己的一已私意,正是當今世上的俗 吏才如此這般。張侯為人慈愛平易,一接觸就看得出來他的心意;所 以他到任還不到一個月,全縣的官士百姓,無不喜愛他仰慕他。
感歎啊!我縣的人民,努力耕種以上繳稅賦。全心全意伺朋皇帝 派來的官吏,真是無所不至。即使相繼死在苛刑之下,也從沒敢有怨恨之心;唯獨對於事情的是非曲直,就有不能昧心作偽的,有時只能 表達在鄉間小巷中的歌謠裡。孔子編刪《詩經》三百篇,讚美的詩歌 只有一成,意在諷刺的卻有九成,正是以此來疏導百姓的情感,引導他們說出心聲。如《十月之交》、《雨無正》邁樣的歌謠,即便以周幽王、厲這樣的暴虐,也無法禁絕。如今的有些重臣們一起向皇上迚言,不提官吏們的無良,反而詬罵我們的百姓,認為世風澆薄、人心不古。邁兩百年來仁愛、孝悌、忠誠、樸實的民風民俗,難道到如今就偏偏變得惡劣淺薄了嗎?
張侯剛到任管事時,便遇到了倭寇來犯的警訊。海賊從沿海而來, 深入內陸上百里,紛紛不絕地攻到城下。張侯安然鎮靜地抵禦來犯之敵。即便在兵荒馬亂之中,也不肯沿習以前的惡劣做法,攪擾百姓。自從前年海賊來襲,縣裡總是在倭寇到達前就封閉城門,又嚴禁出城。 老百姓僅剩一點糧米菜蔬,還都被官吏役卒奪走。靠近縣城的人們,扶老攜幼,來到城下呼號;城上卻沒有人回應他們,只坐視他們在鋒刃下掙扎。更有甚者,還說要抓捕可疑的人,將他們當作海賊的間諜 而殘忍地處死他們。想來含冤受苦的百姓,不單單是死在倭寇手裡的。像這些以前的行徑,今年都沒有了。可見賢人君子的出現,哪裡一定 要很久的時間!彷彿及時的雨水澆灌萬物,哪有什麼邊際?由此可知, 張侯當真不是今天的一般俗吏。就在一月之間,我們對他的敬愛、仰慕之情便如此之深;想來知道我縣民風民俗不是薄惡的人,也沒有比 得張侯的了。所以我樂於向人們講述他的事。
張侯名叫張牧,是辛丑年的迚士,山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