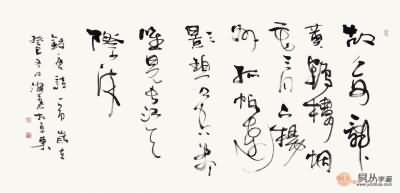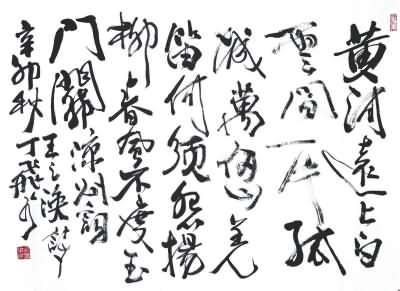李相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構(「構」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時中橋胡蘆生者善卜,聞(「聞」字下原本有「女」字,據明抄本刪)人聲,即知貴賤。李公患腦瘡,又欲挈家居揚州,甚愁悶。及與崔氏弟兄訪胡蘆生,蘆生好飲酒,人詣之,必攜一壺,故謂為胡蘆生。李公與崔氏各攜錢三百。生倚蒲團,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蘆不為之起,但伸手請坐。李公以疾後至,胡蘆生曰:「有貴人來。」乃命侍者掃地,即畢,李公已到,未下驢,胡蘆生笑迎執手曰:「郎君貴人也。」李公曰:「某貧且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貴哉?」蘆生曰:「紗籠中人,豈畏迍厄。」李公請問紗籠之事,終不說。遂往揚州。居於參佐橋,使院中有一高員外,與藩往還甚熟。一旦來詣藩,既去,際晚又至,李公甚訝之。既相見,高曰:「朝來拜候,卻歸困甚。晝寢,夢有一人,召出城外,於荊棘中行,見舊使莊戶,卒已十年,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為物所誘,且便須回,某送員外去。卻引至城門。某謂之曰,汝安得在此。雲,我為小吏,差與李三郎當直。某曰,何外李三郎?曰,住參佐橋之(明抄本、陳校之作「知」)員外。與李三郎往還,故此祗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曰,某饑,員外能與少酒飯錢財否?子城不敢入,某與城外置之。某謂曰,就是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已令於城外與置酒席,且奉報好消息。」李公微笑,數年,張建封僕射鎮揚州,奏李公為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且言張公不得為宰相。甚懷怏,因令於便院中,看郎宦有得為宰相者否?遍視良久:曰,並無。張公尤不樂。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報雲,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公大喜,因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說。李公竟為宰相也。信哉,人之貴賤分定矣。(出《逸史》)
【譯文】
丞相李藩,曾經居住在東洛,三十歲的時候,還沒當官。他的夫人是崔構的女兒,李藩寄住在岳丈崔家,受到冷淡的待遇。當時,中橋有個算命的叫胡蘆生。只要聽到人說話的聲音,就能知道貴賤。李藩患腦瘡,又想攜帶家眷搬到揚州去住,心情很不好,便和崔家的兩兄弟去拜訪胡蘆生。胡蘆生好喝酒,別人找他算命,必須拿一壺酒,所以被稱做胡蘆生。李藩和崔家兄弟各帶了三百文錢。胡蘆生靠在蒲團上,已經半醉。崔家兄弟先到了,胡蘆生也不站起來,只打個手勢,請他們坐下。李藩有病,走在後面。胡蘆生說:「有貴人來。」於是叫僕人掃地。剛掃完地,李藩就到了。還沒等他下驢,胡蘆生就笑著拱手來迎接說:「您是貴人啊!」李藩說:「我很窮又有病,並且全家要搬到幾千里之外去,有什麼貴呢?」胡蘆生說:「紗籠中人,怎麼能怕挫折呢?」李藩請教他什麼是紗籠?胡蘆生一直不肯說明。李藩搬到揚州的參佐橋。節度使的官署裡有一個高員外,與李藩來往密切。一天早上他來看望李藩,很快就走了。當天晚上又來了,李藩有點奇怪。高員外說:「早晨看望你回去後,覺得很睏,就在白天睡了一覺。夢中一個人將我領到城外,在荊棘中行走。忽然看見了過去的佃戶,這個人已經死了十多年了。他對我說:「員外不應該來這裡,是受了誘惑,應該馬上回去,我送員外回去。」將我領到城門外。我對他說:「你怎麼在這裡。」他回答說:「我是衙役,被分配到李三郎處當差。」我說:「什麼地方的李三郎?」他回答說:「住在參佐橋。我知道員外和李三郎來往密切,所以在這裡等候。」我說:「三郎怎麼能夠這樣?」他回答說:「因為是紗籠中人。」再問,他就不肯說了。他又對我說:「我餓了,員外能不能給我點酒菜錢財?你們的城裡我不敢進,我就在城外等著。」我對他說:「就到李三郎家裡取,行不行?」他說:「要是那樣,就同殺我一樣。」然後我就醒了,我已經派人去城外擺一桌酒席,並且來向你報告這個好消息。」李藩微笑著不說話。幾年後,張建封被任命為僕射,鎮守揚州。他請示朝廷聘任李藩為巡官校書郎。恰巧有個新羅和尚來到揚州,他很會看相。他說張建封不能當宰相,張建封聽了很不高興,便叫新羅和尚看一看官署裡的官員有沒有能當宰相的。和尚看了半天,說:「沒有。」張建封更加不高興了,說:「有沒有官員沒在院子裡?」差官報告說:「李巡官沒來。」張建封叫人去找,不一會兒李藩來了。和尚走下台階去迎接,對張建封說:「李巡官是紗籠中的人,僕射您也趕不上他。」張建封非常高興,便問什麼是紗籠中人?和尚說:「如果是宰相,陰間必然派人以紗籠守護著,恐怕被異物所傷害,其餘的官員都沒有這種待遇。」這時才知道胡蘆生所說的是指李藩能當宰相啊!不能不相信,人的貴賤是早由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