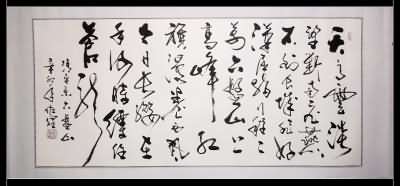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裡人。裡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干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為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為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游,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於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為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為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為卑官,不為人知。與吳興沈彥文為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為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台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闃無所觀。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為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於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褲,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發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裡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捨於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出《宣室至》)
【譯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武陵郡的開元寺有個僧人法號惠照,看起來已經衰老了,身體也很瘦弱。他好預言人的吉凶福禍,而且都能說中。性格狷介孤獨,從不跟許多人在一起說笑,常常關著門獨自一人呆在屋裡,周圍也沒有侍童陪伴。他總跟鄉下人討飯吃。有個八十多歲的鄉下人說:「惠照法師住在這雖六十年了,他的容貌跟從前沒有一點兒不同。只是不知他到底有多大歲數。」後來,有個叫陳廣的,從孝廉舉為武陵的官吏。此人愛好佛教,有一天便來寺廟拜謁。他遍訪了各位僧人,最後來到惠照的房間。惠照見到陳廣後,又悲又喜地說:「陳君為什麼這麼晚才來呢?」陳廣十分驚訝,因為自己從不認識惠照。他問惠照道:「從未與法師交往過,法師為何驚訝我來晚了呢?」惠照說:「這件事不是馬上就能說清楚的,應當與你詳細地談一宿的。」陳廣覺得奇怪,過了一天,他又來到惠照住宿的地方,向他請教這件事。惠照於是講道:「我是劉氏的後代,彭城人。是劉宋孝文帝的玄孫。曾祖父是鄱陽王劉休業,祖父是劉士弘。他們都精通《史記》。先輩們因有文學才能而負有盛名,為南齊竟陵王子良所熟識,子良招納優秀的文學人才,先輩們也都參預了。後來又在齊梁兩朝時作官;作過會稽縣令。我出生於梁朝普通七年(公元526年)夏季五月。三十歲開始在南陳求官,到陳宣帝時,作過小官,不為人知道。我跟吳興的沈彥文是詩酒之交。後來長沙王陳叔堅與始興王陳叔陵都廣泛召集賓客,非常有聲勢。賓客們依仗自己受到權貴的寵愛,互相之間不服氣。我與沈彥文都在長沙王的門下。等到興王陳叔陵被殺害後,我與沈彥文擔心長沙王也不能倖免,那就會殃及我們,於是一起潛逃了。我們躲在山林裡,用橡栗充飢,穿一件短上衣,無論隆冬盛夏也沒有其他衣服可以更換。有一天,一個老僧來到我們住的地方對我說:『你的骨相很奇特,不會患病的。』沈彥文也向他施禮、求藥,老僧說:『你沒有劉君那樣長的壽命。有什麼法子呢!即使吃了我的藥,對你也沒有補益呀。』說完就告辭走了,臨走時又對我說:『塵世間因名利爭強好勝,到頭來能得到什麼呢?只有佛教徒能不追求功名利祿呀!』我很敬佩他說的話,從此,一連十五年不問世事。後來又與沈彥文一起到了建業,當時陳王朝已經滅亡。宮闕殘廢,台城冷落,荊棘叢生,景陽宮也掛滿了蛛網,只有空蕩蕩的房子還存在,至於衣冠文物之類,全都蕩然無存。老朋友偶而相遇時,扯起衣襟直抹眼淚,哽咽著說:『陳後主驕奢淫逸,終於為隋文帝所滅,實在可悲啊!』我更是止不住地抽泣。我又詢問陳後主與陳氏諸王的下落,得知他們都進了長安。我與沈彥文提著一個布口袋,沿路乞討,終於到了關中,我是長沙王原來的賓客,他對我恩遇十分深厚。聽說他遷移到瓜州去了,就又趕到那裡去拜見他。長沙王從小到大都過的是豪華日子,而且又很早就封為王爺而顯貴起來;所以,如今雖在流放之中,仍然不能營生。當時他正與沈妃暢飲,我與沈彥文再次拜倒在他面前時,長沙王悲痛地哭了好長時間,然後灑淚而起,對我說:『一日之內家國淪亡,骨肉離散,難道這不是天命麼?』從此我便留在瓜州住了幾年。長沙王死了幾年後,沈彥文也死了。於是,我落髮為僧,遁跡於會稽山佛寺中,在那裡共住了二十年。我那時已經一百歲了,雖然容貌乾枯瘦削,但筋骨強健體力不衰,尚能日行萬里,便與一位僧人一起到了長安。當時唐朝皇帝佔有天下,建立年號為武德,共有六年。從此之後,我或者住在京都洛陽,或者雲遊長江兩岸,就連三蜀五嶺,也沒有我不去的地方。如今我已二百九十歲了,平生屢經嚴寒酷暑,從未有過小小的疾病。貞元末年,我在這座寺廟裡曾夢見一個偉丈夫,他衣冠楚楚,仔細一看,原來是長沙王。我把他接進屋請他坐下,談起往事來他非常傷感,就像他在世時那樣。他對我說:『十年後,我的六世孫陳廣,會到此郡為官,法師一定要好好記著這件事。』我便問他道:『王爺現在幹什麼?』答道:『在陰間作官,官位很高。』然後哭泣著說:『法師仍然健在,而我已六世為人了!實在令人悲傷啊!』夢醒之後,我便記下你的名字,放在經書箱子裡。到去年,已經過了整整十年,我便以你的姓名,打聽郡裡的人,聽說你沒來到我還很驚訝,昨天因為去鄉里討飯,遇見一位官吏,便向他打聽,終於打聽到你來了。等到你來我這裡時,見你很像長沙王的相貌,然而從那次作夢到今天,已是十一年了,所以驚訝你來得晚。」惠照講完後,百感交集,老淚縱橫。他拿出經書箱子裡記下的陳廣的姓名給陳廣看,陳廣便再三施禮膜拜,立志奉佛,甘作惠照的門徒弟子。惠照說:「你暫且回去,明天再來。」陳廣接受他的教誨回去了。第二天他又來到惠照的住處,而惠照已經躲走了,不知他去了哪裡。當時是元和十一年。到大和初年,陳廣任巴州掾,在蜀道上突然碰見惠照。陳廣又驚喜,再三禮拜道:「我願棄官不做,跟從師父去作超然物外的雲遊。」惠照答允了他。那天晚上,他倆一起住在客店裡,天還沒亮,陳廣起床時惠照已經走了。從此,一直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惠照自梁普通七年出生,查對南梁歷史,普通七年是丙午年;至唐憲宗元和十年乙末,計二百九十年;這與惠照自己說的歲數,果然相符。筆者常常用南梁和南陳兩朝的歷史,校對惠照所說的內容,發現頗有相同之外,由此更加相信他的話不是欺人之談。
卷第九十三 異僧七
宣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