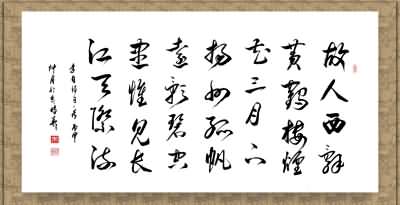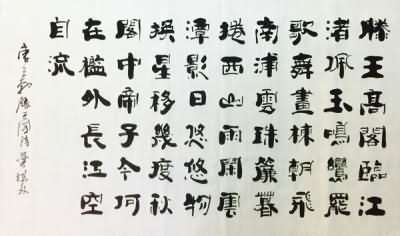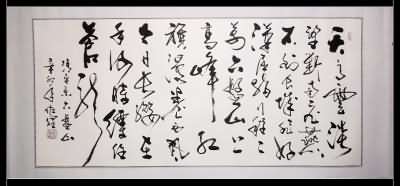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宋史·程迥傳》
: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諉迥,迥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民饑,府檄有訴閉糴及糶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逼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群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眾,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縣大水,亡稻麥,郡蠲租稅至薄,迥白於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全放,恐戶部不從。」迥力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役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舂簸,以養其姑。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為人牧牛,亦干飯以餉祖母。迥廉得之,為紀其事,白於郡,郡給以錢粟。
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迥曰:「斯錢古之除陌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覆言之當路。
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
(節選自《宋史列傳一百九十六》)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縣人。家住在沙隨,靖康之亂時,移居紹興的余姚縣。十五歲時,遭遇父母之喪,孤苦貧窮,飄泊不定,無法自救。二十多歲,才知道讀書,當時戰亂剛剛平息,西北一帶的士大夫大多居住在錢塘,程迥才有了機會被朝廷考察其德行與學業。隆興元年考中進士,擔任揚州泰興縣尉。訓武郎楊大烈有十頃田地,楊大烈死後留下了妻子女兒。不久有人告楊大烈的妻子不是正室,他的財產應該沒收入官,並且追繳十年來所收的租子。部使者把這件事推托給程迥處理,程迥說:「楊大烈死了,財產應當歸他女兒所有。他女兒死後,財產歸她的生母所有就可以了。」百姓鬧饑荒,官府檄文指出有人控告有禁止買米和賣米給外地商人的現象,程迥馬上分析回答說:「努力耕田的人,細米每斗才價值九十五文,受交納稅賦的逼迫,因此不得已才賣米,並不是富裕的家庭。縣境內又不出財貨珍寶,如果不和外地客商交易,交納給官府的錢又從哪裡獲得?現在豪強之人群聚一起,向別人脅迫索取錢財,毆打傷害了很多人,百姓不敢進入市場交易,因此導致缺少糧食。」陳述分析多次,意見被採納才停止。
縣裡發了大水,莊稼沒有收成,郡裡免除百姓的租稅極少,程迥向官府報告說:「這樣作就是逼迫人民流離失所!租稅不可能收到,空留記錄虧欠租稅的賬簿。」於是全部免除了百姓的租稅。郡裡的一些官員還議論說:「朝廷南渡之後,不曾全部免除租稅,恐怕戶部不會答應這樣的做法。」程迥深刻地分析說:「唐朝時損失達到七成,那麼租、庸、調就全部免除。現在損失已經達到十成了,夏稅、役錢還沒有免除,這是仍然施行其中的兩條,不能算是減輕得太多。」爭論才停止。轄境內有個婦女被別人雇去操持家務,以此來奉養自己的婆婆。婆婆被兒媳的孝心感動,每當接到送來的食物,就把手放在額上仰天祈禱。婦女的兒子給別人放牛,也求取飯菜來送給祖母。程迥訪查瞭解了這個情況,為了記錄表彰這件事,向郡裡報告,郡裡給婦女送了錢糧。
調任信州上饒縣。上饒每年繳納租稅數萬石,過去的做法加倍徵收,官吏又巧取斛面米(量米時用手段多征的米)。程迥極力制止杜絕這種現象,曾經說:「縣令和官吏所食用的,都是這地方老百姓的膏血。竟然不想著這種思德,卻橫徵暴斂虐待百姓,天地鬼神難道真的不明察人間的事嗎!」州郡催討經總錢(宋代的一種附加雜稅)非常急迫,程迥說:「經總錢就是古代的除陌錢(唐代一種雜稅),現在這錢徵收的卻是主要賦稅的三倍,老百姓怎麼能夠承受得起?。」反覆把這話說給執政者。
程迥做官對百姓莊重嚴肅,政策寬厚而明睿,政令簡潔而誠信,安撫百姓,用思義開導他們。多年的爭訟,有時候程迥一句話就能調解。奸猾的官吏刁鑽的百姓,都很感激,時間久了就有所悔悟,欺詐的惡俗因此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