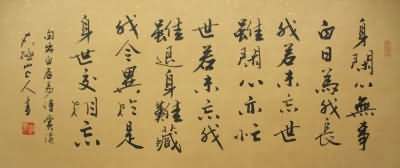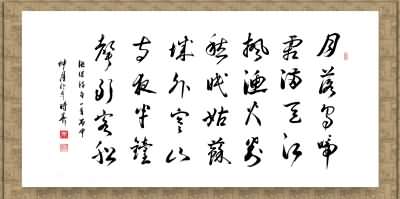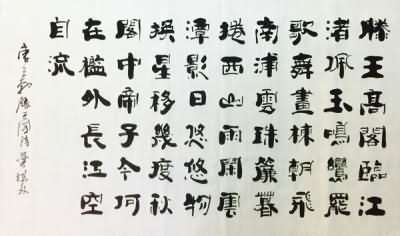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並紙錢佩帶,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才寐,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為太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刻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才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才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尺寸之阻,得達本土。以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益("益"原作"緩",據明鈔本改。)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卻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回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才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雲,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慓之轉切也。(出《博異記》)
【譯文】
隴西李全質年輕在沂州時,曾經整天玩踢球的遊戲。一次天快亮時,在沂州的橫門東庭前閉目休息。忽然有一個穿紫衣服、頭戴圓斗笠的人直奔他面前來,並且說:"奉命追趕。"全質問:"什麼人追我?"穿紫衣的人說:"不是我追你,另有人追你。"不一會兒,一個穿綠衣服的人過來,說:"奉命追趕。"那人說話時神色惶急,看情勢是無法挽回的了。全質說:"你難道有什麼需求?"綠衣人說:"奉命追趕,怎敢說有什麼需求。"紫衣人對綠衣人說:"不用追。"用手一揮,讓綠衣人離開橫門。紫衣人乘機對全質說:"剛才蒙您所問所需,難道你能兌現你的許諾嗎?"全質問:"你需要什麼?"那人回答說:"一條犀牛佩帶罷了。"全質回答說:"行。"說完那人就不見了。主管踢球的人報說:"開始踢球。"全質就派人辦置犀牛佩帶。當天晚上,備辦了酒肉、紙錢、和佩帶,在橫門外焚燒了。這天夜裡,全質剛剛入睡,就夢見穿紫衣、戴圓斗笠的人來拜謝說:"承蒙您賜給我佩帶,慚愧極了,無以報答,然而你這一生將要遭水難,只要你有危難的時候,我一定前來相助。"等到太和初年漲大水,全質已經做了太平軍副將,兼做監察。一次有緊急軍務,要從中都到梁郡城,向西走到離百歇橋二十里的地方,水深而冰薄,全質平素又不熟悉水運,軍命嚴厲緊急,片刻不可停留,隨從都嚇得面色如土。全質只好信手拿著韁繩,聽天由命地向前走。才走了三十幾步遠,有一個人從後面追上來,大聲呼喊著:"不要到那裡去,往這邊走!我熟悉那條路,安全而且近。"全質讓那人上了馬,把韁繩交給他,自己跟從那人而行。走了還不到三里,道路只是有點泥濘,而沒有絲毫阻礙,就到達了駐地。然後全質用財物去酬謝那個人,那人堅決推辭。全質又堅持要酬謝,那人回答說:"你依靠我才來到這,我也許不該謙讓,現在你又為了我才這樣做,又何苦呢?"終於不肯接受。全質認為這樣的人很難得,就想收留他。不一會兒,再來找他,他已經不知去向了。回來後仔細回想,那人穿紫衣,頭戴圓斗笠,豈不是橫門外遇見的那個人嗎?開成初年,奉命入關,回來後住在壽安縣。未睡到半夜,心情煩悶,當時天又非常黑暗,不得已走出旅館。走了三里多地,天下起大雨,回旅館已不可能。不一會兒,馬前見一人,全質問他是誰,回答說是驛站傳遞文書的郵牒。那人一直在馬前走。那天夜裡,前邊寸步遠的地方都看不清。那人常用前邊路上的景物來引路,有時說有樹,有時說有樹樁,有的地方說危險,有的地方說是小土丘,有的地方說是絕路。路上一切危險可能造成的傷害,全質全都避免了。又過了很長時間,到了三泉驛站,稍休息一下。全質剛剛下馬,去查訪剛才那個郵牒,想酬謝他,那人已經不見。問隨行的人打聽那人的衣著打扮,原來是穿紫衣服,頭戴圓斗笠的,又不是橫門外的那個人嗎?會昌壬戌年,濟陽漲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坐一條船,他對水給全質造成的恐懼非常驚訝,打聽原因,全質敘述了以前的事情。並且又說:"我本來不怕水,紫衣人屢次有應驗,所以一遇到水情,就戰戰兢兢地反覆揣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