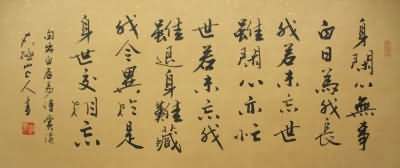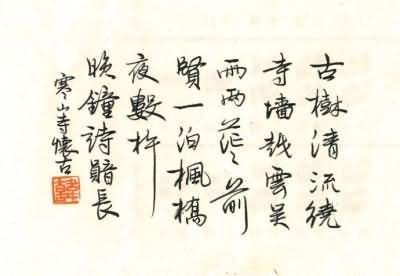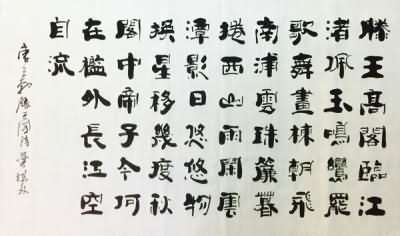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縉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氐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為天曾權祿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致於此,亦命也。今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鹹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甑甑已聞呼父名也,輒紿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征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淒愴,歔欷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殖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出《前定錄》)
【譯文】
柳及是河南人,貞元年間的登科進士柳殊的兒子。家在澧陽,曾經到南海遊覽,元帥因為他父親在官僚紳士中很有名望,就讓他在廣州作了個假署員。不久,娶了會長岑家的女兒。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甑甑。柳及以親戚老人離家太遠,不能接來一起住的名義,帶著妻和子回到澧陽安居。還沒過第二年,又以家裡供給不足的名義,自己乘一輛車重遊南海。到了以後謊說家在蒙山。在武仙又娶了沈氏。柳及在郡府作會計,獨有沈氏和她的母親在縣裡的公館住。當時正是秋天,夜幕降臨之後,天晴月皎。忽然在窗戶裡看見一個小孩,用手招呼沈氏說:「不要怕,不要怕,我是你丈夫的孩子。」他說的話和表情態度,都清清楚楚。沈氏把這事告訴了他的母親。她母親就問那小孩是什麼人,有什麼要求。小孩回答說:「我叫甑甑,去年七月死的,所以來辭別。凡是未成年死的人,沒有滿七歲,因為活著的時候沒有什麼罪過,就不受什麼報應。即使不能馬上托生,大多數被天曹有權勢的人所驅使。我也當了差役,只送文書來往於地府間,天曹記錄人間的善和惡,每月都送給地府一次。這其間有空暇的時間,也可以閒溜一會兒。沈氏就告訴他說:「你父親在郡裡當會計,馬上就要回來了。」不一會柳及回來,沈氏就把事情全都告訴了柳及。柳及不信,說:「荒郊野外,該是有妖怪假托人事,怎麼知道不是山精鬼魅幹的事呢?」有天晚上,又在窗戶裡看見那小孩用手招呼柳及。柳及開始還懷疑,一本正經地盤問他,等那小孩把來龍去脈都說出來,才知道他不是別的鬼,就哽咽涕泣,又問他夭折的原因。回答說:「去年七月,我玩耍得了痢疾。醫藥都沒有用,所以才死了。這也是命啊。現在被天曹收我作差役,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托生。」柳及說:「你既然屬於冥司,那麼人生先定的事就會知道了,能不能給我檢看一下窮富命運生死的事,知道了就來告訴我。」小孩回答說:「好。」後來一天晚上小孩來了。說:「冥府有一座大城,貴賤等級,都有自己的位置,好像棋子那樣分佈。世間的人將要死時,或者半年,或者幾個月內,就先在城中招呼他的名,當時我已經聽到呼叫父親你的名了。」就哄騙他走了。然後小孩偷偷地對沈氏說:「我父親的名已經在冥府裡被招呼了,不能在人間活多長時間,以後有人求娶你的人,特別小心不要答應,如果有姓周的,職務在軍隊裡,就可以答應,一定會白頭偕老,衣食充足美好。」小孩所說的近來的事,沒有不應驗的。後來有一天晚上又來說:「我已經拘役有限,不能再到人間來了,從此永別了。」言語淒惋悲愴,哽咽著走了。過了四個月以後,柳及果然死了。沈氏也在不久後漂泊在南海一帶,有時也有求婚的,都沒有答應。後來長沙有個小將姓周,拿本郡部隊的錢財,在廣州作買賣,請求娶沈氏,一說就同意了。到現在還在。平昌的孟弘微與柳及認識。把他的事都記錄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