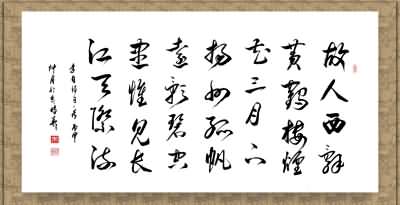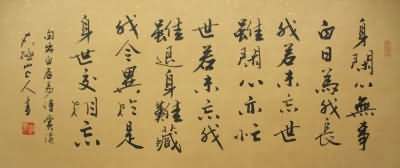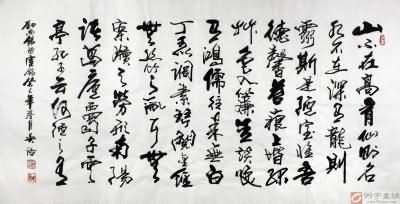原文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明末齊大亂,妻為北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畜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母弗聽。
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其所自來。曰:「余竊面倩鄰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洩累弟。且日一啖,饑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曰:「將助樵采。」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
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年幼,宜閉之。山中虎狼多。」師曰:「午前不知何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曰:「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少休。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歎其賢,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
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欻有虎至。眾懼而伏。虎竟銜誠去。虎負人行緩,為訥追及。訥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眾慰解之,哭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況為我死,我何生焉!」遂以斧自刎其項。眾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湧,眩瞀殞絕。眾駭,裂之衣而約之,群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劙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依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詢弟所,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人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內城。
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忽共嘩言:「菩薩至!」仰見雲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十年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捽訥跪。眾鬼囚紛紛籍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哄騰震地。菩薩以楊柳枝遍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裡門,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蘇,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為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瘥。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為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訥乃去。每於沖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
逾年,達金陵,懸鶉百結,傴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道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踔前後。一少年乘小駟,屢視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以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命脫騎載訥,連轡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銜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經宿。適張別駕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裡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
別駕無長君,子之。蓋適從游矚也。誠具為兄告。言次,別駕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敘。別駕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別駕曰:「僕亦齊人。貴裡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蕩無家室。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別駕瞠而視,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別駕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黑固山半年,生汝兄。又半年,固山死,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別駕曰:「汝以弟為子,折福死矣!」別駕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別駕四十有一,為長;誠十六,最少;訥二十二,則伯而仲矣。
別駕得兩弟,甚歡,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別駕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裡,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吊。忽見訥人,暴喜,怳怳以驚;又睹誠,喜極,不復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別駕母子至,翁輟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別駕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婢媼廝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為。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蘇。別駕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銜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憒憒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為別駕墮。一門團圞,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為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
聊齋之張誠白話翻譯:
河南有個姓張的人,祖籍是山東人。明朝末年山東大亂,他的妻子被清兵搶走了。張某常年客居河南,後來就在河南安了家,娶了妻子,生了個兒子取名張訥。不久,妻子死了,張某又娶了一個妻子,也生了個兒子,取名張誠。繼室牛氏性情凶悍,常嫉恨張訥。把他當作牛馬使喚,給他吃粗劣的飯食。又讓張訥上山砍柴,責令他每天必須砍夠一擔。如果砍不夠,就鞭打辱罵,張訥幾乎無法忍受。牛氏對親生的兒子張誠,則像寶貝一樣,偷偷給他吃甜美的食物,讓他到學堂去讀書。
後來,張誠漸漸長大了,性情忠厚、孝順。他不忍心哥哥那樣勞累,暗暗地勸說母親,牛氏不聽。一天,張訥進山砍柴,還沒砍完,忽然下起暴雨,他只好躲避在岩石下。雨停了,天也黑了,他肚子太餓,只好背著柴回家。牛氏看到砍的柴不夠數,就發怒不給飯吃。張訥飢餓難忍,只得進屋躺下。張誠從學堂回來,看見哥哥沮喪的樣子,就問:「病了?」張訥說:「餓的。」張誠問他原因,張訥把實情說了。張誠悲傷地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張誠懷裡揣著餅來送給哥哥吃。哥哥問他餅是哪來的,他說:「我從家中偷了面,讓鄰居做的。你只管吃,不要說出去。」張訥吃了餅,囑咐弟弟說:「以後不要這樣了!事情洩漏了會連累弟弟的。況且一天吃一頓飯雖然餓,也不會餓死。」張誠說:「哥哥本來身體就弱,怎麼能多打柴呢!」
第二天,吃過飯後,張誠偷偷上山,來到哥哥砍柴的地方。哥哥見到他,驚奇地問:「你來幹什麼?」張誠回答說:「幫哥哥砍柴。」張訥問:「誰叫你來的!」他說:「是我自己來的。」哥說:「別說弟弟不能砍柴,就是能砍,也不行。」催促他快回去。張誠不聽,手腳並用扯著柴禾,還說:「明天要帶斧頭來。」哥哥過去制止他,見他的手指出血,鞋也磨破了,心痛地說:「你不快回去,我就用斧頭割頸自殺!」張誠才回去了。哥哥送了他一半路,才又回去。張訥砍完柴回家,又到學堂去,囑咐弟弟的老師說:「我弟弟年齡小,要嚴加看管,不要讓他出去,山裡虎狼很多。」老師說:「上午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已經責打了他。」張訥回到家,對張誠說:「不聽我的話,挨打了吧?」張誠笑著說:「沒有。」第二天,張誠懷裡揣著斧頭又上山了。哥哥驚駭地說:「我再三告訴你不要來,你怎麼又來了?」張誠不說話,急忙砍起柴來,累得汗流滿面,一刻不停。約摸砍得夠一捆了,也不向哥哥告辭,便回去了。老師又責打了他。張誠就把實情告訴老師,老師讚歎張誠的品行,也就不禁止他了。哥哥屢次勸阻他,他始終不聽。
一天,張訥兄弟倆同其他一些人到山中砍柴。突然來了一隻老虎,眾人都害怕地伏在地上,老虎徑直把張誠叼走了。老虎叼著人走得慢,被張訥追上。他使勁用斧頭砍去,正中虎胯。老虎疼得狂奔起來,張訥再也追不上了,痛哭著返回來。眾人都安慰他,他哭得更悲痛了,說:「我弟弟不同於別人家的弟弟,況且是為我死的,我還活著幹什麼!」接著就用斧頭朝自己的脖頸砍去。眾人急忙救時,斧頭已經砍入肉中一寸多,血如泉湧,昏死過去。眾人害怕極了,撕了衣衫給張訥裹住傷口,一起扶他回家。後母牛氏哭著罵道:「你殺了我兒子,想在脖子上淺淺割一下來搪塞嗎?」張訥呻吟著說:「母親不要煩惱!弟弟死了,我絕不會活著!」眾人把他放到床上,傷口疼得睡不著,只是白天黑夜靠著牆壁坐著哭泣。父親害怕他也死了,時常到床前餵他點飯,牛氏見了總是大罵一頓。張訥於是不再吃東西,三天之後就死了。
村裡有一個巫師「走無常」,張訥的魂魄在路上遇見他,訴說了自己的苦難,又詢問弟弟在什麼地方。巫師說沒看見,但反身帶著張訥走了。來到一個都市,看見一個穿黑衣衫的人,從城中出來。巫師截住他,替張訥打聽張誠。黑衣人從佩囊中拿出文牒查看,上面有一百多男女的姓名,但沒有姓張的。巫師懷疑在別的文牒上,黑衣人說:「這條路屬我管,怎麼會有差錯?」張訥不信張誠沒死,一定要巫師同他進城。城中新鬼舊鬼來來往往,也有老相識,問他們,沒有人知道張誠的下落。忽然眾鬼一齊叫:「菩薩來了!」張訥抬頭看去,見雲中有一個高大的人,渾身上下散放光芒,頓時世界一片光明。巫師向張訥賀喜說:「大郎真有福氣!菩薩幾十年才到陰司一次,給眾冤鬼拔苦救難,今天你正好就碰上了!」於是拉張訥一起跪倒。眾鬼紛紛嚷嚷,合掌一齊誦慈悲救苦的禱詞,歡騰之聲震天動地。菩薩用楊柳枝遍酒甘露,水珠細如塵霧。不一會兒,雲霞、光明都不見了,菩薩也不知哪裡去了。張訥覺得脖子上沾有甘露,斧頭砍的傷口不再疼痛了。巫師仍領著他一同回家,看見村裡的門了,才告辭去了。張訥死了兩天,突然又甦醒過來,把自己見到和遇到的事講了一遍,說張誠沒有死。後母認為他這是編造騙人的鬼話,反而辱罵他。張訥滿肚子委屈無法申辯。摸摸創痕已全好了,便支撐著起來,叩拜父親說:「我將穿雲入海去尋找弟弟。如果見不到弟弟,我一輩子也不會回來了。願父親仍然以為兒已死了。」張老漢領他到沒人的地方,相對哭泣了一陣,也沒敢留他。
張訥離家出走後,大街小巷到處尋訪弟弟的下落。路上盤纏用光了,就要著飯走。過了一年,來到金陵。一天,張訥衣衫襤褸佝僂著身子,正在路上走著,偶然看見十幾個騎馬的過來,他趕緊到路旁躲避。其中有一人像個官長,年紀有四十來歲,健壯的兵卒,高大的駿馬,前呼後擁。隨行的一個少年騎一匹小馬,不住地看張訥。張訥因為他是富貴人家的公子,不敢抬頭看。少年勒住馬,忽然跳下馬來,大叫:「這不是我哥哥嗎!」張訥抬頭仔細一看,原來是張誠!他握著弟弟的手放聲大哭。張誠也哭著說:「哥哥怎麼流落到這個地步?」張訥說了事情的緣由,張誠更傷心了。騎馬的人都下來問了緣故,並告知了官長。官長命騰出一匹馬給張訥騎,一同回到他的家裡。張訥這才詳細地問了張誠後來的經過。
原來,老虎叼了張誠去,不知什麼時候把他扔在了路旁,張誠在路旁躺了一宿。正好張別駕從京都來,路過這裡。見張誠相貌文雅,愛憐地撫摸他。張誠漸漸甦醒過來,說了自己的家鄉住處,可是已經相距很遠了。張別駕將他帶回家中,又用藥給他敷傷口,過了幾天才好了。張別駕沒有兒子,就認他作兒子。剛才張誠是跟隨張別駕去遊玩回來。張誠把經過全部告訴哥哥,剛說完,張別駕進來了,張訥對他拜謝不已。張誠到裡面,捧出新衣服,給哥哥換上;又置辦了酒菜敘談離後經過。張別駕問:「貴家族在河南有多少人口?」張訥說:「沒有。父親小時候是山東人,流落到河南。」張別駕說:「我也是山東人。你家鄉歸哪裡管轄?」張訥回答說:「曾聽父親說過,屬東昌府管轄。」張別駕驚喜地說:「我們是同鄉!為什麼流落到河南?」張訥說:「明末清兵入境,搶走了我的前母。父親遭遇戰禍,家產被掃蕩一空。先是在西邊做生意,往來熟悉了,就在那兒定居了。」張別駕驚奇地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張訥告詬了他,張別駕瞠目結舌。又低頭想著什麼,急步走進內室。不一會兒,太夫人出來了,張訥兄弟兩人一同叩拜。拜畢,太夫人問張訥說:「你是張炳之的孫子嗎?」張訥說:「是。」太夫人哭著對張別駕說:「這是你弟弟啊!」張訥兄弟倆不知是怎麼回事。太夫人說:「我跟你父親三年,流落到北邊去,跟了黑固山半年,生了你的這個哥哥。又過了半年,黑固山死了,你哥哥補官在旗下,做了別駕。如今已解任了,常常思念家鄉,就脫離了旗籍,恢復了原來的宗族。多次派人到山東打聽你父親的下落,沒有一點消息。怎麼會知道你父親西遷了呢!」於是又對別駕說:「你把弟弟當兒子,真是罪過!」張別駕說:「以前我問過張誠,張誠沒有說過是山東人。想必是他年幼不記得了。」就按年齡排次序:別駕四十一歲,為兄長;張誠十六歲最小;張訥二十二歲為老二。別駕得了兩個弟弟,非常歡喜,同他們住在一間屋裡,盡述離散的端由,商量著回歸故里的事情。太夫人怕不被容納。張別駕說:「能在一起過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分開過。天下哪有沒有父親的人呢?」於是就賣了房子,置辦行裝,定好日子起程。
回到家鄉,張訥和張誠先到家中給父親報信。父親自從張訥走後,妻子牛氏也死了,孤苦伶仃,對影自歎。忽然見張訥回來,驚喜交加,恍恍惚惚;又看到了張誠,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流淚。兄弟倆又告訴說別駕母子來了,張老漢驚呆了,也不會哭,也不會笑了,只呆呆地站著。不多會兒,別駕進來,拜見父親。太夫人抱住張老漢相對大哭。看見婢女僕人屋裡屋外都站滿了,張老漢不知如何是好。張誠不見母親,一問,才知已經死了,哭得昏了過去,有一頓飯功夫才甦醒過來。張別駕拿出錢來,建造樓閣。請了老師教兩個弟弟讀書。槽中馬群歡騰,室內人聲喧鬧,居然成了大戶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