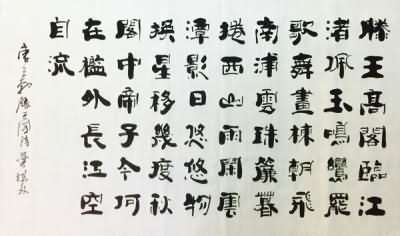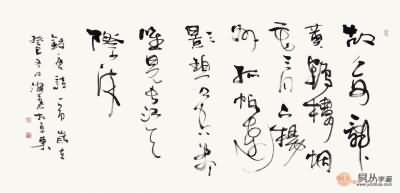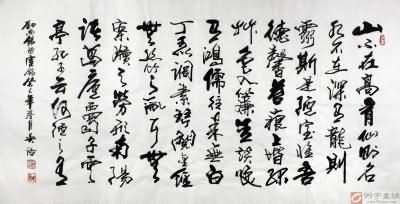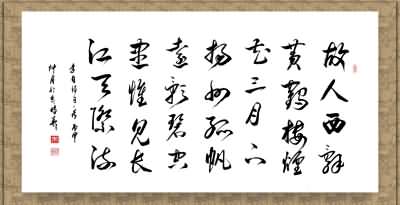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捨會,既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耶!」其僚佐鹹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余。後迫衣食,乃具妝東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宴游極歡。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週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捨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參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發,其驛者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過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參怒曰:「我天子使,眾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參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參聆其音似李徵。參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參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參即降騎。因問曰:「李君,李君,何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問(「問」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曠阻且久矣。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為御史而出使乎?」參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台清峻,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參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為不我見,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為人矣,安得見君乎?」參即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厘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啖之。既至漢陰南,以飢腸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為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籲天,俯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參且問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撐突。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機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托,其可乎?」參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儘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為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念我化為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為繼書訪妻子,但雲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夙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參亦泣曰:「參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參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為我傳錄,誠不敢列人之閾,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參即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參閱而歎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參亦與之敘別,久而方去。參自南回,遂專命持書及撐賻之禮,寄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虢略來京詣參門,求先人之柩。參不得已,具疏其事。後參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參後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譯文】
隴西的李徵,是皇族的後代,家住在虢略。李徵小時候學識淵博,善於寫文章,二十歲就得到州府的推薦,當時被稱為名士。天寶十年春,他在尚書右丞相楊沒主考下考中進士。幾年後,被調補任了江南尉。李徵性情疏遠隱逸,恃才孤傲,不能屈從於卑劣的官吏,常常鬱鬱不樂,悶不作聲。每次與同僚聚會,酒酣之後,他就看著這群官吏說:「我竟然與你們為伍了嗎?」他的同僚都嫉恨他。等到卸了任,他就回到家裡,閉門不與任何人來往。一年多以後,他家的衣食不保,他就準備了一些衣物東遊吳楚之間,向郡國長吏求取資助。吳楚一帶的人聽到他的名聲本來已經很久了,等到他到了,人家都大開著館門等著他。對他招待得特別慇勤,他宴游極歡。臨走的時候,給他優厚的饋贈都填滿他的口袋。他在吳楚將近一年,得到的饋贈特別多。回虢略的路上,住在汝墳的旅店中,他忽然得病發狂,鞭打他的僕從,打得僕從無法忍受。這樣過了十幾天,病情更重。不久,他夜裡狂跑,沒有人知道他到哪兒去了。家僮循著他跑走的方向找他,等著他。一個月過去了,他也沒回來。於是,僕人騎上他的馬,帶著他的財物遠遠地逃走了。到了第二年,陳郡袁參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詔出使嶺南,乘坐驛站的車馬來到商於地界。早晨要出發的時候,驛站的官吏解釋說:「路上有虎,而且吃人,所以從這兒過的人,不是白天沒有敢走的。現在還早,請在這兒多住一會兒,決不可現在就走。」袁參生氣地說:「我是天子的使者,人馬這麼多,山澤裡的野獸能怎樣?」於是他命令立即出發。走了不到一里,果然有一隻老虎從草叢中突然跳出。袁參非常吃驚。很快,虎又藏身回草叢裡了。那虎用人的聲音說道:「奇怪呀,差點傷了我的老朋友!」袁參聽那聲音象李徵。袁參和李徵同時登進士第,兩個人的交情極深,離別有些年頭了,忽然聽到他的話,既驚訝又奇怪,而且沒法推測。於是就問道:「你是誰?莫非是老友隴西子嗎?」虎呻吟幾聲,像嗟歎哭泣的樣子,然後對袁參說:「我是李徵,希望你少等一下,和我說幾句話。」袁參從馬上下來,問道:「李兄啊李兄,因為什麼而至此呢?」虎說:「我自從和你分手,音信遠隔很久了,你沒有什麼變化吧?現在這是要到哪兒去?剛才見到你,有兩個官吏騎馬在前,驛站的官吏拿著印口袋引導,難道是當了御史而出使外地嗎?」袁參說:「最近有幸被列入御史之列,現在這是出使嶺南。」虎說:「你是以文學立身的,位登朝廷的殿堂,可謂昌盛旺達了,況且你一向清廉高尚,盡職盡責英明謹慎,特別與眾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老朋友居於這等地位,很值得慶賀。」袁參說:「以前我和你同時成名,交情甚厚,不同於一般的朋友。自從分離,時間象流水一樣過去了,想企望你的風度和儀容,真是望眼欲穿。沒想到今天在這裡聽到你的念舊之言。既然這樣,那麼你為什麼不見我呢?為什麼要躲藏在草莽之中?咱們是老朋友的情分,難道應該這樣嗎?」虎說:「我現在已經不是人了,怎麼能見你呢?」袁參便詰問是怎麼回事。虎說:「我以前客居吳楚,去年才回來,途中住在汝墳,忽然有病發狂跑到山谷之中,不久就用左右手著地走路。從此我覺得心更狠了,力氣更大了。看看胳膊和大腿,已經長出毛來了。看到穿著衣服戴著帽子在道上走的,看到背負東西奔走的,看到長著翅膀飛翔的,看到長有羽毛奔馳的,我就想吃下他,到了漢陰南,因為飢腸所迫,碰上一個人很肥,就把他捉住吃了。從此就習以為常。不是不想念妻子兒女,不是不思念朋友,只因為行為有負神祇,一旦變成野獸,有愧於人,所以就不見了。天哪!我和你同年登第,交情向來很厚,今天你執管王法,榮耀親友,而我藏身草木之間,永不能見人,跳起來呼天,俯下去哭地,身毀無用,這果真是命嗎?」於是他就呻吟感歎,幾乎不能自勝,於是就哭泣。袁參問道:「你現在既然是異類,為什麼還能說人話呢?」虎說:「我現在樣子變了,心裡還特別明白。所以有些唐突,又怕又恨,很難全說出來。幸虧老朋友想著我,深深諒解我莫可名狀的罪過,也是一種希望。但是你從南方回來的時候,我再遇上你,一定會不認識你了。那時候看你的軀體,就像我要獵獲的一個東西,你也應該嚴加防備,不要促成我的犯罪,讓世人取笑。」又說:「我和你是真正的忘形之交,我將求你辦一件事,不知是不是可以?」袁參說:「多年的老朋友,哪有不可的呢?是什麼事,你儘管說!」虎說:「你還沒答應,我怎麼敢說。現在既然已經答應了,難道還能隱瞞嗎?當初我在客棧裡,有病發狂,跑進荒山,兩僕人騎著我的馬帶著我的財物逃去。我的妻子兒女還在虢略,哪能想到我變成異類了呢?你要是從南方回來,給我捎個信給我的妻子,只說我已經死了,不要說今天的事。希望你記住。」又說:「我在人世間沒有資財,有個兒子還年幼,實在難以自謀生路。你位列仕宦的行列,一向主持正義,昔日的情分哪是他人能比的,一定希望你念他孤弱,時常資助他幾個錢,以免讓他餓死在路上,也就是對我大恩大德了。」說完,又是一陣悲泣。袁參也哭泣著說:「我和你休戚與共,那麼你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兒子,應當盡全力,怎麼還能擔心我做不到呢?」虎說:「我有舊文章幾十篇沒有留行於世上,雖然有過遺稿,但是都散失了。你給我傳錄一下,實在不敢列入名家的行列,但是希望能傳給子孫。」袁參就喊僕從拿來筆墨,隨著虎的口述作記錄。近二十章,文品很高,道理深遠。袁參讀後讚歎再三。虎說:「這是我平生的真實情感,哪敢希望它傳世呢?」又說:「你奉王命乘坐驛站車馬,應該是特別奔忙的,現在耽擱了這麼久,誠惶誠恐。和你永別,異途的遺憾,怎麼說得完呢?」袁參從南方回來,就專門派人把書信和辦喪事的禮物送給李徵的兒子。一個多月以後,李徵的兒子從虢略來到京城拜訪袁參,要找他父親的靈柩。袁參沒有辦法,就詳細地述說了這件事。以後袁參從自己的俸祿中拿出一部分給李徵的妻子兒女,以免他們的饑寒之苦。袁參後來官做到兵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