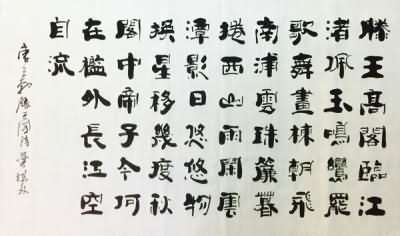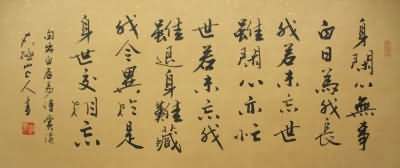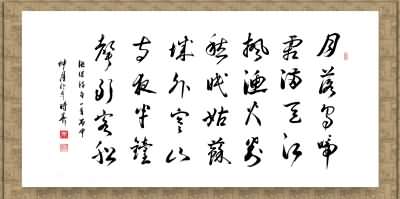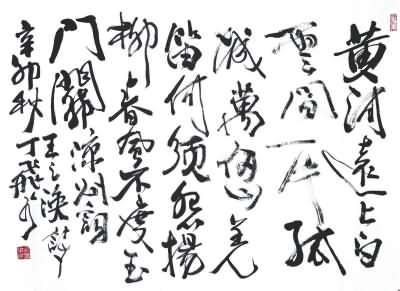知實篇第七九
【題解】
本篇是《實知篇》的姊妹篇。文中列舉了十六個事例,進一步論述了知識來源於經驗這一基本觀點。
王充在開篇即指出:「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他論述:「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並不是「空說虛言」,光憑才智加以推論,而是有事實作為依據的。接著他列舉了十六個大部分與孔子有關的事例,批駁了「聖人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白虎通》)的觀點。為了破除聖人能先知的迷信,王充針對「倍英曰賢,萬英曰傑,萬傑曰聖」(《白虎通》)的論點,進一步引證各種事例,把聖人放到與賢人同等的地位。他指出,聖人「耳聞目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聖賢的區別只決定於他們學習時所付出的勞動程度的不同(聖賢可學,為勞佚殊),並非聖人的耳目有什麼超人的達視之明」,能「知人所不知之狀」。
王充雖然在本篇中提出了重視「效驗」的觀點,但他所指的「效驗」,大多是古人的傳說,古書的記載以及他個人直觀感到的某些事物,並不是指人們的社會實踐。
【原文】
79·1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
【註釋】
准況:通過比較對照,作出類推、判斷。
【譯文】
大凡論述事理的人,如果違背了事實而不舉出證據,那麼,即使道理講得再動聽,說得再多,大家也還是不相信的。我論述聖人不能像神一樣先知,在先知的人中間,並不是只有聖人才能預見,這不只是憑空瞎說,也不只是憑才智類推得巧妙。我的這種看法是有證據的,而且可以證明事實確實是這樣。有哪些事實可以用來證明它呢?
【原文】
79·2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註釋】
公叔文子、公明賈:參見26·14注。
夫子:這裡指公叔文子。
時:適時。
義:指符合儒家的禮義。
豈其然乎:意思是那個傳話的人怎麼把公叔文子說成不言、不笑、不取呢?以上事參見《論語·憲問》。
伯夷:參見1·4注。
芥(jie介):小草,比喻極輕微細小之物。
達視遙見:看得非常透徹、非常遠。
【譯文】
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說:「真的嗎,公叔文子不說話、不笑、不要別人的東西嗎?有這樣的事嗎?」公明賈回答說:「這是由於告訴你的人把話說過了頭。公叔文子在該說的時候才說,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話;高興的時候才笑,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笑;符合禮義才索取,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索取。」孔子說:「難道真是這樣嗎?難道真是這樣嗎?」天下的人,能做到像伯夷那樣的廉潔,不拿別人一點東西,但是從來沒有不說話、不笑的人。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願作出正確的判斷,心有疑問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徹、非常遠,以弄清楚事實,問了公明賈之後才知道了真實情況。孔子不能先知,這是第一條證據。
【原文】
79·3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
【註釋】
陳子禽:名亢,字子禽,春秋時陳國人,孔子的學生。
夫子:指孔子。邦:國,指春秋時期的諸侯國。
與:同「歟」。下句後一「與」同。
溫良恭儉讓: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以上事見《論語·學而》。王充引用這個典故,是為了說明「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所以對這個典故的解釋和《論語》的原意不一樣。尊行:高尚的德行。
以上事見《韓詩外傳》卷八。
【譯文】
陳子禽問子貢說:「孔老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定知道這個國家的政治情況,是他自己打聽來的呢?還是人們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說:「他是憑著溫良恭儉讓這些美德得來的。」溫良恭儉讓是高尚的德行。用高尚的德行對待人,人們就親近他。人們親近他,那麼人們就會告訴他了。既然如此,那麼孔子就是由於人們告訴他才瞭解政治情況的,並不是神而自知的。齊景公問子貢說:「孔老夫子是個賢人嗎?」子貢回答說:「他乃是聖人,哪裡只是個賢人呢?」齊景公不知道孔子是聖人,子貢訂正了他的名稱;陳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麼辦法知道政治情況的,子貢確定了它的實情。既然回答齊景公時說「他是聖人,哪裡只是個賢人」,那麼子貢對子禽也應當說「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聽別人說的」。就子貢回答陳子禽的話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二條證據。
【原文】
79·4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
【註釋】
甑(eng贈):古代蒸飯用的瓦器。
掇(duō多):拾,撿。
以上事見《呂氏春秋·任數》、《孔子家語·困誓》。
【譯文】
顏淵饒火做飯,灰塵掉到飯甑裡,想放開它不管飯就不乾淨了,想把有灰的飯倒掉就要糟踏一些飯,所以就把它挑出來吃了。孔子遠遠地看見了,認為顏淵是在偷飯吃。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三條證據。
【原文】
79·5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
【註釋】
塗:通「途」。道路。狂夫:強暴的人。
投刃:把刀戳在地上,指準備行兇。
厲:同「礪」。磨。
匡:春秋時衛國地名,在今幽銑髂稀N鬃櫻汗?96年,孔子從衛國到陳國去,曾在匡這個地方被當地百姓圍困了五天。事見《論語·子罕》、《史記·孔子世家》。
【譯文】
路上有個狂人,把刀戳在地上等著;野澤中有只猛虎,磨著牙在望著。
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如果不知道或者沒有看見而繼續往前走,那麼就會被狂人殺掉,被老虎吃掉。匡人包圍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該早早地換一條路走,以避開這場災禍。孔子因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這場災禍。以孔子被圍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四條證據。
【原文】
79·6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
【註釋】
子:指孔子。畏:懼,指受到威脅。
以上事見《論語·先進》。
悖(bei倍):亂,暴逆,這裡指弄死、殺害。
【譯文】
孔子在匡地被圍困受到威脅,顏淵最後逃出來。孔子說:「我以為你死了。」如果孔子先知,就應該知道顏淵一定沒有遇害,匡人一定沒有弄死他。看到顏淵回來了,才知道他沒有死;沒有看見他回來的時候,說認為他死了。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五條證據。
【原文】
79·7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
【註釋】
陽貨:參見28·58注。
饋(kui愧):贈送。《論語》作「歸」。豚(tun屯):小豬。這裡指蒸熟的小豬。饋孔子豚:古禮規定,凡大夫贈東西給士,士如果不是在家當面接受,就必須親自去大夫家拜謝。陽貨想請孔子出來做他的助手,孔子不願意,陽貨就利用禮俗,趁孔子不在家時,去送蒸熟的小豬給他,孔子不願見陽貨,又不好違禮,也趁陽貨不在家時登門拜謝。
時:通「伺」。窺伺,伺機。亡:無。這裡指不在家。
反:同「返」。
以上事見《論語·陽貨》。
【譯文】
陽貨想讓孔子來拜見他,孔子不去拜見,陽貨就送給孔子一隻蒸熟了的小豬。孔子探明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謝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見了陽貨。孔子本來是不想見到陽貨的,所以既然去拜會,卻又打探他不在家的時候才去,這種情況說明孔子堅決不想見到陽貨。可是回來時,卻在路上碰上了他。以孔子碰見陽貨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六條證據。
【原文】
79·8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註釋】
長沮(jǔ舉)、桀溺:春秋時兩個不知真實姓名的隱士。耦而耕:兩人各執一耜(si四)一塊耕地。
津:渡口。《水經》潕水註:「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以上事參見《論語·微子》。
論者:指為孔子辯護的人。
【譯文】
長沮、桀溺兩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從旁邊經過,派子路向他們打聽渡口在什麼地方。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麼地方,就不該再去詢問。辯護的人說:「這是想考察一下隱士的品行。」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該自己知道,用不著考察。如果不知道而去問他們,這正好說明他不能先知,這是第七條證據。
【原文】
79·9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
【註釋】
殯:停放棺材。這裡指臨時性的淺葬。衢(qu渠),大路。五甫之衢:五甫衢,一作五父衢,路名,在今山東曲阜縣東南。《左傳·襄公十一年》杜註:「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葬:這裡指正式埋葬。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
鄒曼甫:人名。
防:防山,在今山東曲阜縣東。以上事參見《禮記·檀弓》。
塋(ying營):墳地。
【譯文】
孔子的母親死了,因為孔子不知道他父親的墳墓在何處,所以就把他母親臨時葬在五甫衢。別人看見就認為是正式埋葬了。大概是因為沒找著與他父親合葬的地方,在臨時埋葬他母親時,禮儀很鄭重,所以別人就認為是正式埋葬了。鄰居鄒曼甫的母親把孔子父親的墳墓所在地告訴了他,然後才得以把他的父母合葬在防山。本來在防山就有他父親的墳地,而孔子卻把他的母親臨時葬在五甫衢路旁,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八條證據。
【原文】
79·10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
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
【註釋】
三:再三。指門人說了好幾遍。
泫然:淚流滿面的樣子。
修墓:壘墳頭。以上事參見《禮記·檀弓上》。
【譯文】
合葬之後,孔子先返回家裡。門人後回來,雨下得很大。孔子問:「怎麼回來得這麼晚啊?」門人回答說:「防山的墓倒塌了。」孔子不再說什麼,門人說了好幾遍,孔子才淚流滿面地說:「我聽說,古時候是不修墓的。」如果孔子先知,應當事先知道防山的墓會倒塌,等到門人回來的時候,應該是流著淚等著他們。門人到家之後才知道墓倒塌了,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九條證據。
【原文】
79·11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眾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
【註釋】
太廟:天子或諸侯的祖廟。這裡指周公廟。
以上事參見《論語·八佾》。
疑句首脫「論者曰」三字,遂使文句上下無屬。王充意為孔子不知故問,而責難者認為,孔子實已知而復問。上文「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下文「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其立文並同可證。
引文見《論語·季氏》。
【譯文】
孔子進入太廟,每件事都問。因為他不知道所以才問,這是為了給人們做榜樣。孔子從來沒有進過太廟,廟裡的禮器很多不只是一兩件,孔子即使是聖人,怎麼能都知道呢?辯護的人說:「太廟裡的禮器孔子曾經都見過,實際上他已經知道,然而還要再問一問,這是為了給別人做榜樣。」孔子說:「有了疑問要想到請教別人。」這是說有了疑難才應該問啊!如果說「實際上已經知道,還應當再問,以此給人做榜樣」,那麼孔子通曉「五經」,學生們跟他學習,他也應該再去請教一下別人,以此來給人做榜樣,為什麼孔子只是給學生講課而不請教別人呢?不用自己已經知道五經還去請教別人這種行為給人做榜樣,唯獨以自己已經知道太廟裡的禮器而再問別人這種事給人做榜樣,聖人的用心,怎麼這樣不一致呢?以孔子進太廟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條證據。
【原文】
79·12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捨。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捨,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己,聘召之到,宜寢不住。君子不為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為道不為己,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11)。」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12),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不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13)。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14),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捨,卜還毉絕(15),攬筆定書(16)。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
【註釋】
頓:止,住宿。
洎:據遞修本當作「泊」。泊:通「薄」。輕薄。
親:指父母。徹,通「撤」。撤掉。饌(huan賺):酒食。
周流:周遊列國,四處奔走。
削跡之辱:參見5·6注。
說(shui稅):遊說。非主:不好的君主,這裡指不採納孔子主張的君主。絕糧之厄:參見1·3注。
閔:同「憫」。這裡是憂慮、關心的意思。
塗:泥污。塗炭之中:水深火熱之中。
正:訂正。樂正:指孔子按自己的觀點對當時的音樂加以訂正。他認為通過訂正,音樂就納入了「正道」。
(11)各得其所:指使《雅》、《頌》恢復了各自應有的地位。引文見《論語·子罕》。
(12)最賢之國:指周禮最完備的國家。
(13)魯人獲麟,自知絕也:參見《指瑞篇》51·4和《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14)望:怨恨。沮:沮喪。
(15)毉(yī):同「醫」。
(16)定書:指刪定《詩》、《書》。
【譯文】
主人請賓客飲酒吃飯,或者想請客人住在他的家裡。客人如果聽說他家有輕薄子孫,輕薄子孫必定會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還會關上房門,使客人不能留宿。那麼客人會拿定主意,肯定不會再去了。為什麼呢?因為客人知道被請去了也不會有高興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勞累和侮辱罷了。如果去了沒有什麼可高興的事,又白勞累一場受頓侮辱回來,那是因為客人不瞭解主人的家庭,不瞭解他家的具體情況。人和具體情況都很難預知,吉凶也很難預料。如果孔子先知,就應該知道諸侯已經被讒臣所迷惑,是一定不會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還使自己受到侮辱,聘書和召令到了,也應該擱置起來不去應聘。君子不去做那種毫無益處的事情,不走使自己受到侮辱的路。不必要周遊列國去答應諸侯的聘請,而自取「削跡」的侮辱;不應該白費力氣去遊說那些不會採用自己主張的君主,而自找「絕糧」的災禍。由此說來,孔子似乎並不能先知。為孔子辯護的人說:「孔子自己知道是不會被任用的,聖人憂慮的是『道』行不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多半是想要輔佐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老百姓,所以才答應諸侯的聘請周遊列國,不躲避災禍和恥辱。由於他為的是行道而不是為自己,所以遇到災禍也下怨恨;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為了出名,所以遭受誹謗也不顧忌。」我說:這些都不是真實的。孔子說過:「我從衛國到魯國後,才把《詩》的樂曲進行了整理,使《雅》樂和《頌》樂各得其適當的位置。」這就是說孔子瞭解當時的形勢。根據什麼說他自己知道呢?魯國和衛國,是天下執行周禮最完備的國家,魯國和衛國不能任用自己,那麼天下就沒有什麼國家會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魯國作《春秋》,刪改編定《詩》、《書》。以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這件事來說,可以知道孔子將要應聘時,還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為什麼呢?沒有兆象而無從察考,聖人是沒有根據來作出判斷的。等到魯、衛兩國不任用自己,這才知道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等到魯國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沒有什麼希望了。道行不通,命也完了,徵兆明明白白地顯現出來,內心懷著怨恨、沮喪,只好回去冥思苦想。孔子不停地周遊列國,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禱占卜希望病好,因為死的徵兆還沒有出現,希望能活下去。這樣說來,孔子應聘是因為沒有看到徹底絕望的證據,還希望自己能被任用。等到家中出現了要死人的徵兆,占卜的人回頭就走,醫生也拒絕治療,這才拿起筆來刪定《詩》、《書》。以孔子應聘周遊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一條證據。
【原文】
79·13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
【註釋】
游者:指魚類。綸:指魚線,這裡是釣的意思。
走者:指獸類。矰(ēng增):一種用絲繩繫住的短箭,這裡是射的意思。走:《史記》作「飛」,《龍虛篇》22·12亦作「飛」。
其猶龍邪:相傳孔子曾向老子問禮,老子作了解答,而孔子認為老子的解答很玄妙,所以把老子比做龍。引文參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文字稍有不同。
所從上下:指龍的活動。《龍虛篇》22·12說:「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這裡也兼指老子對孔子所作的玄妙的解釋,像龍那樣,忽上忽下,不可捉摸。
精氣交連:王充認為萬物都是「氣」構成的。同一類物是同一種「氣」所構成的,可以互相溝通。
【譯文】
孔子說:「魚類可以釣到,獸類可以射獲。至於龍,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它能乘著雲風上天。今天見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龍一樣吧!」聖人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龍,一個是人,一個是物,龍的活動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都是事,孔子為什麼不能知道呢?如果老子是神,龍也是神,聖人也是神,那麼神的活動應該有共同的規律,他們的精氣可以互相溝通,為什麼會不知道呢?以孔子不知道龍和老子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二條證據。
【原文】
79·14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註釋】
閔子騫:參見28·2注。
間:離間,非議。昆弟:兄弟。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意思是,由於閔子騫能掩蓋父母兄弟的過失,因而人們對他的父母兄弟沒有可非議的話。引文參見《論語·先進》。瞽叟:參見9·4注。像:參見5·6注。治廩(lǐn凜):修理穀倉。浚(jun俊)井:淘井。
豫:通「預」。預先。
據上文例,「見」字後當有「言之」二字。
【譯文】
孔子說:「閔子騫真是孝順啊!別人在他和他父母兄弟之間說不了挑撥離間的話。」虞舜是個大聖人,他在掩蓋親屬的錯誤方面,應該超過閔子騫。舜的父親瞽叟和異母弟象讓他修理穀倉和淘井,打算藉機殺害他。舜應當看出他們有要殺害自己的意思,應該早早地規勸他們預先防止事情的發生,既然無可奈何了,也應該躲開或裝病不幹。為什麼要使他父親和弟弟構成謀殺自己的罪名,使人們知道這件事而指責他的父親和弟弟,以至萬世之後還有人在談論呢?以虞舜不能預見這件事來說,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三條證據。
【原文】
79·15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既設,。。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為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
【註釋】
事見《尚書·金縢》。
壇:祭祀用的土台。。。(shan善):經過除草、平整供祭祀用的地面。。。:同「策」。參見63·7注。。。祝:祭祀時應用的祝文,這裡是讀祝文之意。後一個「不」:通「否」。
卜三龜:參見63·8注。
聖人:指周公。立法:建立法制。這裡指決定事情。
【譯文】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續武王的壽命。設置了祭壇,讀完了祝文以後,還不知道上天答應了自己的請求沒有,於是就用龜甲占卜了三次,結果兆象都很吉利。如果聖人是先知的,周公就應當知道上天已經答應了自己的請求,不必緊接著又用龜甲占卜三次。知道聖人不以個人的意見來決定事情,所以周公還要乞求天命,並且把祝文秘藏起來不讓人看見。由於天意很難知道,所以三次進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來加以對照。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於是就根據兆象的指示去辦事。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四條證據。
【原文】
79·16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
【註釋】
晏子:參見17·2注。聘:出使。
堂:宮殿,朝堂。趨:小步快走。
晏子解之:晏子解釋自己的行動時說:「古禮上規定,在朝堂上,國君走一步,臣子要走兩步,當時魯君走得快,我就不得不走得比魯君更快;授玉時,魯君彎腰給我,我為表示比魯君地位低得多,所以只能跪下來接了。」事見《韓詩外傳》卷四及《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
【譯文】
晏子出使到魯國。使臣在朝堂上不應該小步快走,而晏子卻快步走了;君王授與玉時,使臣不應該跪著接,而晏子卻跪下來接了。學生們感到奇怪而去請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就去請教晏子。晏子解釋之後,孔子才明白。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五條證據。
【原文】
79·17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註釋】
陳賈:戰國時齊國大夫。孟子:參見1·3注。
管叔:參見42·10注。殷:這裡指武庚。武王滅商後,封紂王的兒子武庚於殷(在今河南安陽)。
畔:通「叛」。事見《史記·魯周公世家》。
與:同「歟」。
事見《孟子·公孫丑下》。
處其下:指周公排行在管叔之下。
【譯文】
陳賈問孟子,說:「周公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孟子回答說:「是聖人。」又問:「周公派管叔去監視武庚,後來管叔等人叛亂了,這兩件事都有嗎?」孟子回答說:「是有的。」又問:「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亂而派他去的呢?還是不知道而派他去的呢?」孟子回答:「不知道才派他去的。」又問:「如此說來,聖人尚且也有過錯嗎?」孟子回答說:「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過錯,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嗎?」孟子是個講求實際的人,既說周公是聖人,又認為他處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預知管叔會叛亂的。聖人不能先知,這是第十六條證據。
【原文】
79·18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強力不倦,超逾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11),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
【註釋】
賜:端木賜,即子貢。參見3·3注。貨殖:做買賣。
億:通「臆」。猜測,估計。中(hong眾):猜中。指猜中行情。引文參見《論語·先進》。
居積:囤積居奇。
貴賤:指物價漲落。
陶朱:參見3·2注。
識:通「志」。記住。
巧商:善於巧妙地推算。
較:通「皎」。顯著。
竅:小孔。引申為細微之物。
倫等:同輩,一般人。
(11)洞聽潛聞:聽得非常清楚,連極小的聲音都可以聽到。
【譯文】
孔子說:「子貢不聽從天命而去經商營利,他猜測市場行情常常很準確。」孔子責備子貢善於囤積,善於估計物價漲落的時機,多次都能抓住時機,所以賺了很多錢,跟陶朱公一樣富有。由此看來聖人的先知,也不過是像子貢屢次猜中行情一樣。聖人也是根據一定的跡象和徵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然後經過判斷而得出結論。聖人見到異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稱,是由於學得多而記得住。聖人巧於推算,善於估計,見識廣,記得多,從微小的苗頭看到明顯的結局,如同根據今天的事物進行推測而預見到千年以後的情況一樣,這可以說是才智浩如淵海了。孔子能夠看到細微而不明顯的事物,思考問題透徹,是由於他的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才超過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並沒有超人的視力,能知道別人所不能知道的情況。如果看得透徹看得遠,聽得清楚無所不聞,能與天地交談,能跟鬼神說話,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那才稱得上是神而先知,與一般人大不一樣。但是,現在聖人耳聞目見,與一般人沒有什麼差別;遇到的事情看到的東西和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比賢人略微高明一點罷了,怎麼能說像神一樣無可比擬呢?聖人跟賢人一個樣,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稱為聖人,那麼聖人與賢人只不過是區別才能大小的稱呼,並不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名號。怎麼來證明這個道理呢?
【原文】
79·19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歡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所言莒也(11);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12)。」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13),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為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
【註釋】
齊桓公:參見3·2注(12)。莒(jǔ舉):齊國附近的一個小國,在今山東莒縣一帶。仲甫:又作「仲父」。這是齊桓公對管仲的尊稱。
東郭牙(yu與):即東郭郵,也稱東郭垂,春秋時齊國人。
賓:主管接待的官。延:引,請。延而上之:將他引上殿堂。
據遞修本「管」字下應補「仲」字。
鐘鼓:兩種打擊樂器,這裡表示婚慶喜事。
衰絰(cuīdie崔迭):衰,生麻布制的喪服。絰:麻制的喪帽和腰帶。古人喪服胸前縫綴粗麻布叫衰,圍在頭上的散麻繩叫絰,纏在腰間的散麻繩叫腰絰。這裡用來表示喪事。怫(fei費)然:憤怒的樣子。「手足者」,義不可通。此文乃本《呂覽》,「手足」下有「矜」字。矜:手足抖動。
兵革:兵器,指戰爭。
■:據《呂氏春秋·重言》當作「吟」。吟(jin盡):閉口。口垂不吟:口張開而不閉起來。
(11)所言莒也:說的正是「莒」字。古時「莒」字的發音與現在不同,所以口形也不一樣。
(12)這件事見《管子·小問》和《呂氏春秋·重言》。
(13)十二聖:參見15·6注。
【譯文】
齊桓公與管仲商議討伐莒國,謀畫好了還沒有行動而國內的人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問管仲說:「我與仲父商議討伐莒國,還沒有行動,國內的人都知道了,這是什麼原因呢?」管仲回答說:「國內一定有聖人。」一會兒,正好東郭牙來了,管仲說:「一定是這個人了。」於是就派一個管接待的官員把他請到殿堂上,分別按賓主的位置站好。管仲說:「是您說我們要討伐莒國嗎?」東郭牙說:「是的。」管仲說:「我沒想要討伐莒國,你憑什麼說我們要討伐莒國呢?」東郭牙回答說:「我聽說君子善於謀畫,小人善於推測,我是私下推測出來的。」管仲說:「我沒有說要討伐莒國,你根據什麼推測的呢?」東郭牙回答說:「我聽說君子臉上有三種神色:婚慶喜事時,表露出歡樂高興的神色;舉辦喪事時,表露出愁苦哀傷的神色;發生戰爭時,表露出非常憤怒以致氣得四肢發抖的神色。你的口開而不閉,說的正是「莒」字;你的手臂舉起來指,所對著的又是莒國的方向。我私下想國家小而又不服從齊國的諸侯,大概只有莒國吧!因此我就這樣說了。」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於區別事物考察事理,他說「國內一定有聖人」,是真心誠意地說國內一定有。東郭牙來了,管仲說「一定是這個人」,就是說東郭牙是聖人。如果聖人與賢人根本不是一類,管仲明知當時並沒有像黃帝等十二聖之類的人,他就應該說「國內一定有賢人」,不應當說是「聖人」。謀畫好了還沒有行動而國內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說「國內一定有聖人」,這是說聖人能先知。等到看見了東郭牙,說「一定是這個人」,是說賢人就是聖人。東郭牙對事情瞭解得這樣清楚,這和聖人是一樣的啊。
【原文】
79·20客有見淳於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於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為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於生誠聖人也!前淳於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為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
【註釋】
客:指梁惠王的賓客。淳於髡(kūn昆):姓淳於,名髡,戰國時齊國人。梁惠王:參見30·1注。
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字前應補「髡」字。
志:心思。志在遠:心思集中在遠方。指梁惠王聚精會神地在想能跑得很遠的龍馬。龍馬:古時稱身高八尺以上的馬叫龍馬。
謳(ōu歐):唱歌。
屏(bīng丙):屏退,打發開。
以上事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因緣:根據,憑借。准的:「准」和「的」都是目標,這裡用作動詞,意即射中目標,引申為「判斷準確」。
【譯文】
有個賓客把淳於髡引見給梁惠王,梁惠王一連兩次接見他,淳於髡始終一言不發。梁惠王對此很不高興,因此責備那個賓客說:「你讚揚淳于先生,說管仲、晏嬰都趕不上他,等到他見了我,我並沒有什麼收穫。難道我不值得跟他談話嗎?」這個賓客把惠王的話告訴了淳於髡。淳於髡說:「本來嘛,我前一次見惠王時,他的心思放在遠處,後一次見他時,他的心思在音樂上,我因此沒有說話。」賓客把淳於髡的話一一匯報給惠王,惠王聽後大吃一驚,說:「哎呀!淳于先生實在是個聖人呀!前一次淳于先生來,正好有人來獻龍馬,還沒來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來了。後一次他來,正好有人來獻歌手,我還沒來得及試聽,正巧他又來了。我雖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那兒。」淳於髡能觀察到惠王的心思在遠處和音樂上,就是成湯、夏禹那樣明察的人,也不能超過他。一個人的心思藏在心裡,從外面發現不了,淳於髡卻能知道。如果把淳於髡這類人看作是聖人,那麼淳於髡就是聖人了;如果認為淳於髡這類人不是聖人,那麼所謂聖人的明智,又怎麼能超過淳於髡對於梁惠王的瞭解呢?通過觀察面部表情來探測內心的活動,都是由於有所依據才能推測得那麼準確。
【原文】
79·21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為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為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11)。後黃龍見成紀(12)。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13)。
【註釋】
楚靈王:參見9·9注。
鄭:春秋時諸侯國,都城在新鄭(今河南省新鄭縣)。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國大夫。
魯、邾、宋、衛:都是春秋時的諸侯國。邾(hū朱):即春秋時的鄒國,在今山東省鄒縣東南。引文參見《左傳·昭公四年》,四國作「魯、衛、曹(在今山東定陶一帶)、邾」。此文云「宋不來」,誤。
趙堯:人名,事跡見《史記·周昌列傳》。符:古代朝廷傳達命令或徵調兵將用的憑證。璽(xǐ喜):皇帝的大印。符璽御史:皇帝的監印官,隸屬於御史大夫。
方與公:《史記》、《漢書》只注「方與」是縣名,公,其號。疑當是方與縣令。御史大夫:參見11·10注。周昌:漢代沛縣人,高祖時為御史大夫。曾隨劉邦起義,立有戰功,蕭何、曹參等人都很敬佩他。
引文參見《史記·周昌列傳》,文字稍有不同。
以上事參見《史記·張丞相列傳》。
公孫臣:漢文帝時人。
孝文皇帝:即漢文帝劉恆。
土德:據陰陽五行說,朝代的更替是按五行相剋的道理循環的。漢人認為秦朝為水德,而土能勝水,漢取代了秦,故漢朝應為土德。
(11)符:符瑞,吉祥的徵兆。黃:按照陰陽五行說,五行中的土是與五色中的黃相配屬的,漢是土德,出現的符瑞就是黃色。
(12)成紀:地名,舊城在今甘肅省秦安縣北三十里。以上事參見《漢書·文帝紀》。
(13)律:樂律。歷:曆法。
【譯文】
楚靈王召集各國諸侯,鄭國的子產說:「魯、邾、宋、衛四國不會來。」等到各國諸侯聚會時,這四國果然沒有到。趙堯是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對御史大夫周昌說:「你手下的御史趙堯將要代替你的職位。」後來,趙堯果然做了御史大夫。這樣說來,四國諸侯不來參與盟會,鄭子產是根據情理推斷出來的,趙堯做御史大夫,方與公是通過某種狀況觀察出來的。推究情理、觀察狀況,推斷未來,都是有所依據而考察出來的。魯人公孫臣,在漢文帝時上奏章給皇帝,說漢朝是土德,它的吉兆黃龍該要出現了。後來,黃龍果然在成紀這個地方出現了。公孫臣知道黃龍將要出現,是根據樂律和曆法推斷出來的。
【原文】
79·22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逾,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
【註釋】
術、數:指方法、謀略,這裡包括各種推測吉凶的手段。
知:通「智」。
實:事物。
鈞:通「均」。
【譯文】
賢聖的智慧如何,事情應該說已經得到驗證了。賢聖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們的先知,是運用各種術數,或者是善於估計和巧妙的推算,並不是聖人憑空就知道的。神怪與聖賢,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聖人與賢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們動腦筋想問題互有長短;他們對待事情並沒有什麼神怪的地方,因而聖和賢這兩種名號可以相互更換。所以,賢、聖是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稱號;而「神」卻是一種渺茫恍惚無形的事物。事物不同,性質也不會一樣;事物相同,表現也不會是兩樣。聖和神的名號是不同的,所以說聖不是神,神也不是聖。東郭牙因為善於推測所以能知道國家的內情;子貢善於估計所以能夠賺錢。聖人的先知,就是子貢、東郭牙這類人的先知。聖人既然與子貢、東郭牙相同,那麼子貢、東郭牙這類人也就是聖人了,既然如此,聖人與賢人的實質是一樣的而只是名號不同,他們之間才能不一定相差很遠,智慧也不會成倍相差。
【原文】
79·23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為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為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註釋】
太宰:官名,位在卿與大夫之間,掌管國君宮廷事務。一說指春秋末年的吳太宰伯嚭(pi疋)。一說泛指古代某個當太宰的人。
以上事參見《論語·子罕》。
據文意,「聖」字前疑當有「為」字。
有:通「又」。
立:獨立,有主見。指符合禮的規範。
天命:指天道運行之精理。
耳順:一聽到別人說的話,就能辨明是非真假。引文參見《論語·為政》。子貢比孔子小三十一歲,孔子四十歲時,子貢才九歲,王充認為子貢回答太宰問題時,正是孔子三十或四十歲時,這個推算是不正確的。
【譯文】
太宰向子貢問道:「孔子是個聖人吧?他怎麼這樣多才多藝呢?」子貢回答說:「這本來是上天讓他將成為聖人,又使他這麼多才多藝的。」將,就是將要的意思。子貢不說已經是聖人,而說將要成為聖人,是他認為孔子當時還沒有成為聖人的緣故。成為聖人和成為賢人一樣,要修養磨煉自己的操行,操行還沒有磨煉成功的時候,那只能說是將要成為賢人。現在子貢說孔子將要成為聖人,是因為聖人是可以做到的緣故。孔子說:「我十五歲立志於學業,三十歲言行合於禮,四十歲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歲懂得了天命,六十歲一聽到別人說的話,就能辨明是非真假。」從「知天命」到「耳順」,學習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達,這是成了聖人的驗證。還沒有到五六十歲的時候,就不能「知天命」,達到「耳順」的程度,所以就稱之為將要。當子貢回答太宰的問話時,大概是孔子三四十歲的時候吧。
【原文】
79·24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版 權所 有https://FanYi.Cool 古文翻譯庫)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為,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為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為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為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
【註釋】
魏昭王:戰國時魏國國君,名遫(su速):公元前295~前277年在位。田詘(qū屈):人名,生平不詳。
東宮(版 權所 有https://FanYi.Cool 古文翻譯庫):太子住的地方。
市人:指一般人。
敢問:謙詞,自言冒昧,大膽地問。這段話參見《呂氏春秋·審應》。易聖:按文意當為「聖易」。上文作「為聖易」。
【譯文】
魏昭王向田詘問道:「我做太子的時候。聽說先生有這樣的議論,說『做聖人容易』,有這回事嗎?」田詘回答說:「聖人是我所要學著去做到的。」昭王問:「這麼說先生是聖人嗎?」田詘說:「沒有作出功績之前就能知道他是聖人,這是堯對舜的認識;等到有了功績之後才能知道他是聖人,這是一般人對舜的認識。現在我還沒有什麼功績,而王就問我『你是聖人嗎?』敢問大王你也是堯一樣的聖人嗎?」聖人是可能通過學習做到的,所以田詘說做聖人容易。如果聖人卓絕得與一般人大不一樣,是稟受天性自然生成的,那怎麼能學呢?學習做聖人又怎麼能成功呢?田詘說的「做聖人容易」,未必能夠成功;田詘說的「做聖人容易」,也未必是對的。他所說的「聖人是我所要學著做到的」,這大概倒是符合實際的。
【原文】
79·25賢可學為,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11)。」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12)。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13),懦夫有立志;聞柳之惠之風者,薄夫敦(14),鄙夫寬(15),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16)?而況親炙之乎(17)?」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18):「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19)。」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註釋】
賢:當為「聖」之誤字。此處全就聖人為說,作「賢」,明為字誤。
佚:通「逸」。
饜(yan厭):滿足。
以上事參見《孟子·公孫丑上》。
子夏、子游、子張:都是孔子的學生。
冉牛、閔子騫、顏淵:都是孔子的學生。引文參見《孟子·公孫丑上》。伯夷:參見1·4注。
伊尹:參見1·2注。
已:止,指不當官。
速:迅速離開。
(11)引文見《孟子·公孫丑上》。
(12)柳下惠:參見8·3注。
(13)頑夫:貪財的人。頑:貪。
(14)薄夫:刻薄的人。敦:厚道。
(15)鄙:偏激,引申為陝隘。鄙夫:心胸狹隘的人。
(16)而:通「能」。
(17)炙:烤,這裡指熏陶。親炙:直接受到教育熏陶。引文參見《孟子·盡心下》。
(18)宰予:參見11·14注(12)。
(19)引文參見《孟子·公孫丑上》。
【譯文】
聖人可以經過學習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更特殊些罷了,所以賢人聖人的稱號雖有區別,但在仁與智方面是共同的。子貢對孔子問道:「您已經是聖人了嗎?」孔子說:「聖人,我達不到,我只是學習從不滿足,教人從不覺得疲倦而已。」子貢說:「學習不滿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有仁又有智,您就是聖人了。」由此說來,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稱為聖人了。孟子說:「子夏、子游、子張,都學到了聖人的一個方面;冉牛、閔子騫、顏淵,他們學到了聖人的各個方面,但程度不深。」這六個人在當時,都具有做聖人的才能,有的略有聖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備了聖人之才而不夠高明,然而都稱他們是聖人,這說明聖人是可以經過努力學習而達到的。孟子又說:「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輔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召喚,天下太平時出來做官,天下大亂時退去歸隱,伯夷是這樣的人。什麼樣的君王都可以輔佐,什麼樣的百姓都可以召喚,局勢穩定可以做官,社會動亂也可以做官,伊尹是這樣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該離開就趕快離開,孔子就是這樣的人。他們都是古代的聖人。」孟子還說:「聖人,是百代的師表,伯夷,柳下惠正是這樣的人。因此,聽到伯夷品性的人,貪婪的人廉潔了,懦弱的人也長了志氣;聽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厚道了,狹隘的人寬宏大度了。他們興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後知道他們事跡的人,沒有不受感動鼓舞的。難道不是聖人才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嗎?更何況親身受到他們熏陶教育的人呢?」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們稱為「聖人」,說明聖人、賢人同是一類人,可以共用一個稱號。宰予說:「據我看孔子,要比堯、舜賢良得多。」孔子是聖人,宰予應當說「比堯、舜更聖明」,然而他說「賢」,正說明聖、賢差不多,所以聖、賢這兩個名稱可以互相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