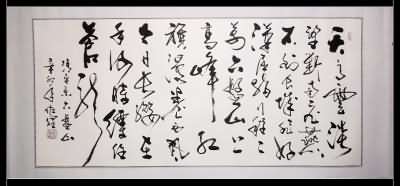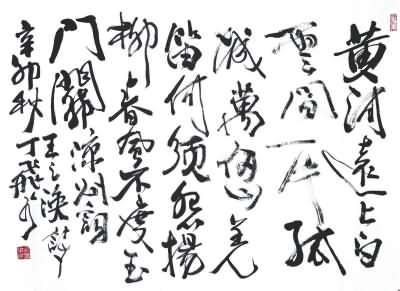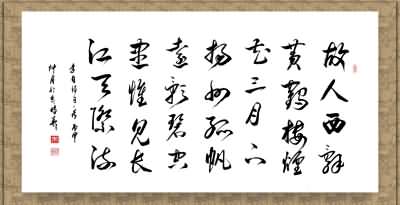刺孟篇第三十
【題解】
本篇是王充譏刺孟子的,所以篇名叫「刺孟」。
王充以記載孟子言行的《孟子》為靶子,抓住其中孟子言行不一,前後矛盾,答非所問,陰陽兩面,無理狡辯的地方,逐一進行揭露和駁斥。例如針對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天故(有意)生聖人」的天命論說法,作者用歷史事實證明完全是「浮淫之語」。對於自認為「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而誰」的孟子,則指出他不是什麼「賢人」,而是個「俗儒」。但對孟子「人無觸值之命」,「天命於操行也」的合理東西,也強辭奪理進行了責難。
【原文】
30·1孟子見梁惠王(1),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2)?」
【註釋】
(1)梁惠王(公無前400~前319年):即魏惠王,戰國時魏國君主。名罃。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公元前361年,魏國都由安邑(在今山西省夏縣西北)遷到大梁(在今河南省開封市),所以魏惠王又稱梁惠王。
(2)以上事參見《孟子·梁惠王上》。
【譯文】
孟子會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頭,你不遠千里而來,要拿什麼使我的國家得利呢?」孟子說:「講仁義就行了,為什麼要說利呢?」
【原文】
30·2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1)?《易》曰:「利見大人(2)」,「利涉大川(3)」,「乾,元亨利貞(4)。」《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5):「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6)。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7),孟子逕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8),違道理之實也。
【註釋】
(1)徑:任意,輕率。
(2)引文見《周易·乾卦》。
(3)引文見《周易·需卦》。
(4)乾:乾卦。《周易》中的第一卦。元:大。亨:順利。貞:卜問。引文見《周易·乾卦》。
(5)不:根據文意,疑「必」之誤。
(6)若:這裡作此講。設:根據文意,疑「言」字之誤。
(7)令:根據文意,疑「今」形近而誤。趣:旨趣,意思。
(8)指:通「旨」,意思,意圖。
【譯文】
利有二種:有貨物錢財的利,有平安吉祥的利。梁惠王說「拿什麼使我的國家得利」,怎麼知道他不是想得到平安吉祥的利,而孟子卻輕率地以貨物錢財的利去責難他呢?《周易》上說:「得此卦見『大人』吉利」,「得此卦過大河吉利」,「得乾卦,大吉大利。」《尚書·秦誓》上說:「老百姓也很看重利啊。」全是平安吉祥的利。實行仁義就會得到平安吉祥的利。孟子一定要姑且先問一問惠王:「你說的使我的國家得利是什麼意思?」要是梁惠王說是貨物錢財的利,才能夠以「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來回答。如今還不知道惠王問的是什麼意思,孟子就輕率地以貨物錢財的利來對答。如果梁惠王確實是問貨財的利,孟子也無法用什麼來證明;如果是問平安吉祥的利,而孟子以貨物錢財的利來對答,那就不符合君主的意圖,也違背了起碼的常識。
【原文】
30·3齊王問時子(1):「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2),養弟子以萬鍾(3),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4)。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5)。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6)?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註釋】
(1)齊王:指齊宣王。時子:齊宣王時的大夫。
(2)中國:國都之中。這裡指齊國國都臨淄城中。
(3)鍾:參見8·10注(5)。
(4)矜:敬重。式:傚法。
(5)陳子:陳臻(h5n真),孟子的學生。
(6)惡(w&烏):怎麼。
(7)以上事參見《孟子·公孫丑下》。
【譯文】
齊宣王問時子:「我想在都城裡給孟子一所房子,拿萬鍾俸祿供養他的弟子,讓大夫和百姓們都有敬重傚法的榜樣。你為什麼不替我跟他說說呢?」時子通過陳子把這事告訴了孟子。孟子說:「時子哪裡知道這樣做不行呢?假使我想富貴,就不會拒絕做齊卿的十萬鍾俸祿來接受這一萬鍾俸祿,我這樣做是為了貪圖富貴嗎?」
【原文】
30·4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1)。」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2)?
【註釋】
(1)居:處。這裡指享受。引文見《論語·裡仁》。
(2)距:通「拒」。距逆:拒絕。
【譯文】
孟子拒絕做齊卿的十萬鍾俸祿,不符合謙讓的道理。「富貴,是人人想得到的,不從正當途徑得到它,就不該享受。」所以君子對於爵位和俸祿,有的推辭,有的不推辭。難道因為自己不貪圖富貴的緣故,就以此來拒絕應當接受的賞賜嗎?
【原文】
30·5陳臻問曰:「於齊,王饋兼金一百鎰而不受(1);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2),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3)。」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行贐(4),辭曰:『歸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5)。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6),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7)?」
【註釋】
(1)饋:疑「歸」字之誤。下文有「歸七十鎰而受」,「歸五十鎰而受」,可一證。章錄楊校宋本作「歸」可二證。歸:贈送。兼金:比一般貴一倍的金子,好金子。
(2)薛:地名。原來是薛國,在今山東省滕縣東南,後被齊兼併,成了齊相田嬰、田文父子的封地。
(3)君:這裡是說孟子二者必居其一的意思,故疑「君」系衍文。《孟子·公孫丑下》無此文,可證。
(4)贐(j@n盡):給遠行者贈送的路費或禮物。
(5)處:處理。這裡指送錢的理由。
(6)貨:財貨。這裡是用財物收買,賄賂的意思。
(7)以上事參見《孟子·公孫丑下》。
【譯文】
陳臻問孟子:「在齊國,齊王送你好金一百鎰,不肯接受;在宋國,送你七十鎰,卻接受了;在薛國,送你五十鎰,也接受了。如果你認為以前不接受禮物是對的,那麼今天接受禮物就錯了;要是今天接受禮物是對的,那麼以前不接受禮物就錯了。老師你在這二者中必居其一。」孟子說:「我都是對的。當時在宋國,我將要遠行,給遠行的人一定要送路費,辭行者說:『送盤費。』我哪能不接受呢?當時在薛國,我害怕出危險有戒心,辭行的人說:「聽說你有戒心,所以為便於有武器進行戒備,送點錢給你做準備吧!』我哪能不接受呢?像在齊國,我就沒有收受禮物的理由。沒有收受禮物的理由而送禮物給我,這是用財物收買我,難道有君子可以用財物收買的嗎?」
【原文】
30·6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己貪,當不受之時己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
【註釋】
(1)上文有「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後文有「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故疑「富」後奪一「貴」字。
【譯文】
金子送來了,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有緣故的,並不是接受的時候就表示自己貪財,當不接受的時候就表示自己不貪財。金子有接受與不接受的道理,而房子也該有接受與不接受的道理。如今孟子不說「自己沒有功績」,或者「自己已辭官了,再接受房子就不合理」,而是說「自己不貪圖富貴」,並用以前拒絕做卿的十萬鍾俸祿來比後來這次一萬鍾俸祿該拒絕的理由。其實以前該享受十萬鍾那麼多的俸祿,這次又怎麼能拒絕呢?
【原文】
30·7彭更問曰(1):「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2),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3);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4)。」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為戒乎?
【註釋】
(1)彭更:人名。孟子的學生。
(2)傳(hu4n賺):轉輾。食:供食,供養。
(3)簞(d4n單):古代盛飯的圓形竹器。簞食:竹籃裡盛的乾糧。
(4)以上事參見《孟子·滕文公下》。
【譯文】
彭更問孟子:「跟隨你的車幾十輛,跟隨的人幾百個,輪流由諸侯供養,不也太過分了嗎?」孟子說:「如果不符合禮義,連一籃子乾糧也不能接受人家的;如果符合禮義,就是舜接受堯的天下,也不能算是過分。」接受堯的天下,跟接受十萬鍾俸祿相比,哪個多呢?舜不拒絕接受天下,是符合禮義的。如今孟子不說「接受十萬鍾俸祿不符合禮義」,而說「自己不貪圖富貴」,這不符合謙讓,怎麼能用來作為鑒戒呢?
【原文】
30·8沈同以其私問曰(1):「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2),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3)。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4)?」曰:「未也。沈同曰(5):『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6):『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7)?』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8)。』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也(9)?」
【註釋】
(1)沈同:人名。戰國時齊國大夫。
(2)子噲(ku4i快):戰國時的燕國君主。公元前320~前312年在位。此君昏庸無能,聽信蘇代和鹿毛壽的話,公元前318年,讓位給專權的燕相子之,自己稱臣。孟子反對這種無視周天子的做法,扇動齊國攻燕,結果燕軍大敗,子之被剁成肉醬。與:給予,授予。
(3)子之:人名。戰國時燕王噲的相。
(4)諸:「之乎」的合音。
(5)曰:疑是「問」之誤。後文有「沈同問燕可伐與?」可一證。又《孟子·公孫丑下》作「問」,可二證。
(6)下文有「彼如曰『孰可以殺之』」,文例相同,故疑「如」上奪一「彼」字。《孟子·公孫丑下》作「彼如曰」,可證。
(7)天吏:指周天子。
(8)士師:官名。周代是司寇的下屬官吏,掌管禁令、獄訟、刑罰。古代是法官的通稱。
(9)以上事參見《孟子·公孫丑下》。
【譯文】
沈司以他的私交問孟子:「燕國可以討伐嗎?」孟子說:「可以。子噲不該把燕國讓給人,子之也不該從子噲手中接受燕國。要是有這樣的人,你喜歡他,不告訴國君,而私自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給了他,而這人,也沒有君王的命令就私自從你手中接受了爵位和俸祿,這樣可以嗎?現在子噲把王位讓給子之跟這有什麼差別呢?」齊國討伐燕國,有人問孟子:「聽說你曾鼓動齊國討伐燕國,有這事嗎?」孟子說:「沒有。是沈同問:『燕國可以討伐嗎?』我回答說:『可以。』他認同就去討伐了燕國。他如果再問:『誰可以去討伐它?』我就會回答說:『只有奉行天命的周天子才能討伐它。』就像現在有個殺人犯,有人問他:『犯人可以殺嗎?』那他將會回答說:『可以。』他如果再問:『誰可以去殺他呢?』那就應該回答說:『只有法官才可以殺他。』如今作為像燕一樣無道的齊國要去討伐燕國,我為什麼要去鼓動它呢?」
【原文】
30·9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1),宜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2)。公孫丑問曰(3):「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4),謠辭知其所陷(5),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6)。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7)。」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8)。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註釋】
(1)慊(qi8竊):滿足,愜意。
(2)知言:這裡是善於分析判斷別人的言辭。
(3)公孫丑:人名。姓公孫,名丑。戰國時齊國人。孟子的學生。
(4)詖(p#坡):通「頗」,不正,偏差。蔽:遮擋,阻礙。這裡是壓抑的意思。
(5)淫:迷惑。
(6)遁:迴避,遁辭:暫時用來應付的話。窮:處境困難。
(7)以上事參見《孟子·公孫丑上》。
(8)福:疑「害」之誤。上言「禍」,禍福常連文,故誤作「福」。下「知其極所當害」述本句,可證。
【譯文】
有人問孟子鼓動齊王討伐燕國的事情,不確實是這樣嗎?沈同問「燕國可以討伐嗎」,這是挾帶私心想使自己的國家去討伐燕國。既然知道他的意圖在討伐燕國為滿足,就應該說:「燕國即使可以討伐,也必須是奉天命的周天子才能夠去討伐它。」這樣沈同的意圖就會斷絕,那麼也就沒有討伐燕國的計劃了。如果不曉得他有這種私心而隨便回答他,是沒有省悟他話中的含意,這是不善於分析、判斷言辭。公孫丑問孟子:「請問老師擅長什麼?」孟子說:「我善於分析、判斷言辭。」公孫丑又問:「什麼叫善於分析、判斷言辭呢?」孟子說:「聽到不公正的話,知道他要壓制誰;蠱惑人心的話,知道他要陷害誰;邪僻的話,知道他要離間誰;吞吞吐吐的話,知道他要為難誰。這些話從他們心裡產生,會危害他們的政治;用來處理他們的政務,就會危害他們的事業。即使聖人重新出現,也一定會聽從我的這番話。」孟子是善於分析、判斷言辭的,並知道言辭可能產生的災禍,以及它最終會導致的危害。聽見沈同的問話,就該知道他說話想表達的東西,知道他要表達東西,那就該知道它最終面臨的危害。
【原文】
30·10孟子有雲(1):「民舉安(2),王庶幾改諸(3)!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4)?而是(5),何其前輕之疾(6),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7),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8),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9)。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
【註釋】
(1)有(yu又):通「又」。
(2)舉:全,都。民舉安:以此為句,跟下文無法銜接,故疑引文有脫誤。《孟子·公孫丑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意思是,齊王如果任用我,那豈只是齊國的百姓得到平安,天下的老百姓也都會得到平安。
(3)庶幾:也許可以。
(4)前所不朝之王:即齊宣王。《孟子·公孫丑下》記載,孟子想去見齊宣王,但又要擺架子,裝病不去。齊宣王派人來看他,他甚至躲到齊大夫景丑氏家。
(5)而:通「如」。
(6)疾:這裡是厲害的意思。
(7)子:根據文意,疑衍文。
(8)三日宿:指孟子捨不得馬上離開齊國,在晝(齊國地名,在今山東省淄博市東北)住了三天,希望齊王能回心轉意,請他回去。
(9)景丑氏:人名。戰國時齊國的大夫。
【譯文】
孟子又說:「齊王如果任用我,那豈只是齊國的百姓得到太平,連天下的老百姓也都會得到太平,齊宣王也許可能改變態度吧!我天天都在盼望著。」孟子離開的這個齊王,難道不是以前不肯去朝見的齊王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以前極端輕視他,而後來又非常重視他呢?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不肯離開前一個齊王,而離開了後一個齊王,這說明後一個齊王比前一個齊王更不賢明,然而在離開後一個齊王的時候,卻捨不得走,在晝住了三天,而對前一個不很賢明的齊王,不肯去朝見卻躲在景丑氏家裡。為什麼孟子的操行前後不一樣,對待齊王的態度,先後也這樣不一致呢?
【原文】
30·11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劈人臧倉毀孟子(1),止平公。樂正子以告(2)。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3)。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4)。」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5)?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6);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7)?
【註釋】
(1)嬖(b@閉):寵愛。嬖人臧倉毀孟子:魯平公要會見孟子,臧倉說:孟子辦他後死的母親的喪事遠遠超過先死的父親的喪事,像這種人你還是不見為好。
(2)樂(yu8月)正子:姓樂正,名克。魯平公的臣子。孟子的學生。
(3)尼:阻止,阻撓。
(4)以上事參見《孟子·梁惠王下》。
(5)定:決定。這裡是標準的意思。
(6)冀:希望。
(7)前言:指「予之不遇魯侯,天也」這句話。
【譯文】
再說,孟子在魯國的時侯,魯平公想見他。寵臣臧倉譭謗孟子,勸阻了魯平公。樂正子把這事告訴了孟子。孟子說:「幹事,是有力量暗中支配他;不幹,也是有力量暗中阻止他。干與不幹不是人能決定的。我得不到魯侯的任用,是天意。」孟子以前在魯國得不到任用,後來在齊國得不到任用,沒有什麼兩樣,把以前得不到任用歸咎於天,把如今得不到任用就歸咎於王,孟子的論述究竟以什麼為標準呢?孟子的主張在齊國得不到實行,齊王不任用他,就像在魯國有臧倉一類人譭謗他一樣,這也是「不幹,有力量在暗中阻止他」。這都是由天命決定得不到任用,並非是由人能決定的。既然這樣,離開齊國,為什麼不直截了當走掉,而要在晝留宿三天呢?天命不該在齊國被任用,齊王不採納他的主張,天難道會在三天的時間裡改變意志使他被任用嗎?在魯國則歸咎於天,斷絕了念頭不存在任何希望;在齊國則歸咎於王,就感到也許會有希望。照這樣說,有關不被任用的解釋,完全在於人怎麼說了。有人說:「剛離開時,還不可能確定天命。希望在三天之內,齊王又把他追回去,天命或許在三天之內才能做出決定,所以這樣做是可以的。」那麼照這樣說,齊王最初讓他離開,就不是天命了?如果天命在三天之內才能確定,魯平公等了三天,也許拋棄了臧倉的意見,改用樂正子的建議去見孟子。孟子歸咎於天,豈不太早了嗎?如果三天之內魯平公去見了孟子,孟子對前面說過的話又怎麼解釋呢?
【原文】
30·12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1):「夫子若不豫色然(2)。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3)。』」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而誰也?吾何為不豫哉(4)!」
【註釋】
(1)充虞(y*於):孟子的學生。
(2)豫:愉快,高興。
(3)引文參見《論語·憲問》。
(4)以上事參見《盂子·公孫丑下》。
【譯文】
孟子離開齊國,充虞在路上問他:「看來老師好像有些不高興的樣子。
從前,我聽老師說過:『君子不抱怨天,不責怪人。』」孟子說:「那時是那時,現在是現在。歷史上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這期間肯定不會有著名於世的人物。從周初以來,已有七百多年了。按年數,已經超過了;照時勢來考察,是該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了。難道上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嗎?如果想使天下治理好,在當今這個時代,除了我還有誰呢,我為什麼不高興呢!」
【原文】
30·13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1),而堯又王天下(2);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3),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4)。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5),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
【註釋】
(1)帝嚳: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堯的父親。
(2)王(w4ng忘):當王,做王。
(3)千歲:這是根據古代對經傳的解釋,夏四百年,商六百年而來的,並非確數。
(4)卒:終於。這裡是後來的意思。
(5)浮:虛浮。這裡是沒有根據的意思。淫:過分,無節制。
【譯文】
孟子說「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何以見得呢?帝嚳是聖王,而堯又做了天下的聖王;堯把王位傳給舜,舜又做了天下的聖王;舜把王位傳給禹,禹又做了天下的聖王。這四位聖王統一天下,是連接出現的。從夏禹到商湯將近一千年,商湯到周代也大致是這樣。從周文王開始,後來傳給周武王。周武王死了,周成王和周公旦共同治理天下。從周初到孟子的時候,又經過了七百年而沒有聖王出現。「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的證據,在哪個朝代有過呢?說「每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的話,又是誰說的呢?發表議論不用事實考查驗證,而輕信沒有根據,過分誇大的話,自己不被任用離開齊國,卻有不高興的神色,這不是孟子賢明的表現,而是跟庸俗儒生沒有區別的證明。
【原文】
30·14五百年者(1),以為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註釋】
(1)下文有「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疑「五」字前奪一「雲」字。後文「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文例相同,可證。
【譯文】
孟子說「五百年」作為天生聖王的期限。又說「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他的意思認為天真想使天下治理好,就應該在五百年之內降生聖王。按孟子的說法,是說天有意識地降生聖人的。那麼五百年,是天降生聖人的期限嗎?如果是期限,天為什麼不降生聖王呢?可見五百年不是聖王降生的期限,所以他不降生,然而孟子還是相信這個說法,這說明孟子不懂得天。
【原文】
30·15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1)?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逾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2),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
【註釋】
(1)上文言「以其數,則可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於是本句才發問「何謂數過?何謂時可乎?」故疑「可」前奪一「時」字。下文「數過,過五百年也」,「又言『時可』,何謂也?」以相應,可證。
(2)或:有。
【譯文】
「從周初以來,已經七百多年了。按年數,已經超過了;照時勢來考察,是該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了。」什麼叫超過了年數?什麼叫照時勢考察該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年數就是時勢,時勢就是年數。超過年數,指已經超過了五百年。從周初到今天七百多年,已經超過了二百年。假設有聖王降生,已經錯過了時間,又說「該是出現聖王和『名世者』的時候」,這話怎麼說呢?
【原文】
30·16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
同乎?異也?如同,為再言之(1)?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己又以生矣(2)。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3)。聖王出,聖臣見矣(4)。言「五百年」而已,何為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5)。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
【註釋】
(1)根據文意,疑「為」上奪一「何」字。「何為再言之」與下文「何為言其間」,句例相同,可證。
(2)以:通「已」,已經。
(3)根據文意,疑「聖」下奪一「王」字。下文「聖王出,聖臣見」,可證。
(4)見:同「現」。
(5)上文言「五百年」聖王與聖臣是否會同時出現,故疑「聖」下奪一「臣」字。
【譯文】
說「過五百年一定有聖王出現」,又說「這期間一定有著名於世的人物出現」,這裡說的著名於世的人物跟聖王是同一回事呢?還是兩回事呢?如果是同一回事,為什麼要重說一遍呢?如果是兩回事,「著名於世的人物」指的是什麼人呢?是說孔子、孟子之類人,教誨青年,使愚笨的人覺悟嗎?那麼已經有了孔子,而你自己卻又出生了。如果說的是輔佐聖王的聖臣嗎?就該與聖王同時出現。聖王出現,聖臣就該出現。這樣,說「五百年」就行了,為什麼要說「在這期間」呢?如果不是說五百年時間,是說五百年的中間嗎?這是說二三百年時間,那麼聖臣就不會跟每五百年時間出現的聖王相遇了。像這樣,孟子說「這期間一定有著名於世的人物」,究竟指的是誰呢?
【原文】
30·17「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捨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有王者,若為王臣矣(1)。為王者、臣,皆天也。己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2),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註釋】
(1)若:則。
(2)浩然:水勢浩大,不可阻擋。比喻心胸寬闊、毫無牽掛。這是針對孟子「浩然有歸志」的話說的。
【譯文】
「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要是想治好天下,除了我還有誰呢?」孟子說這樣的話,不是自認為應該做聖王,而是認為有聖王出現,則該做聖王的臣子。孟子認為做聖王、做王臣,都是天命決定。既然自己命定不該把天下治理好,又不肯心地坦然地住在齊國,卻懷恨在心,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這就不符合天命了。
【原文】
30·18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1),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2)。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3),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4),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5)。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6):「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7),可食而食之矣(8)。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9),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10)。」
【註釋】
(1)通:交往,這裡是交流的意思。功:成績。這裡是成果的意思。事:這裡與「功」相對,當是成果,產品的意思。
(2)梓(!子)匠:木工。輪輿:造車工。
(3)悌:弟弟順從兄長。
(4)待:對待。這裡指教育。
(5)志:志向。這裡是指目的,動機。
(6)孟子:疑是衍文。本文記述問答,每段開頭列出人名,文中則省略,可證。(7)功:功能。這裡是用處的意思。
(8)食(s@飼):通「飼」。這裡是給人吃的意思。
(9)畫:讀劃,割開,劃破。墁(m4n慢):通「■」,織物做的車蓋。
(10)以上事參見《孟子·膝文公下》。
【譯文】
彭更問孟子:「讀書人不幹事白吃飯,可以嗎?」孟子說:「如果人們不交流成果互換產品,用多餘補充不足,那麼農民就會有餘糧,婦女就會有餘布。你如果能使它們溝通,那麼木工、造車工都能從你那兒找到飯吃。如果這兒有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兄長,堅守古代聖王的道義,以此教育後代的學者,卻不能從你那兒找到飯吃。那你為什麼只看重木工、造車工而輕視遵循仁義的人呢?彭更說:「木工、造車工,他們的目的是要以此謀生。君子遵循道義,他們的目的也是要以此謀生嗎?」孟子說:「你為什麼要考慮他們的目的呢?他們對你有用處,可以管飯就給他們飯吃。再說,你是按人的目的給飯吃呢,還是按對你有用給飯吃?」彭更說:「按目的給飯吃。」孟子說:「如果有人在這裡,毀壞屋瓦割開車蓋,他的目的是以此謀生,那你給他飯吃嗎?」彭更說:「不給。」孟子說:「那麼你並不是按人的目的給飯吃,而是按對你有用給飯吃的。」
【原文】
30·19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1)。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2)。癡狂人之志不求食(3),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4),以作此鬻賣於市(5),得賈以歸(6),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7),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於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8),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眾多,己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9),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10),可謂「御人以口給」矣(11)。
【註釋】
(1)詰(ji6潔):查問,反駁。
(2)遨(4o熬):遊戲。
(3)人之:疑「之人」之誤倒。下文「遨戲之人亦不求食」,可證。
(4)不:本句的意思是,求食者做的,應該使許多人都得到利益的事,故疑是「共」字之誤。
(5)作此:句難通。故疑是「所作」之誤。鬻(y)育):賣。
(6)賈(ji4價):通「價」,價格。這裡是代價的意思。
(7)比:這裡是同、相等的意思。
(8)博戲:馬戲,用六箸十二棋。
(9)超距:跳遠。
(10)以:用。這裡是「採用」、「聽取」的意思。
(11)御:阻止,對付。口:口齒。給(j(己):敏捷,伶俐。口給:這裡是花言巧語、強嘴利舌的意思。引文參見《論語·公冶長》。
【譯文】
孟子舉出毀壞屋瓦,割開車蓋的人,想用它來反駁彭更的話。因為他知道毀壞屋瓦、割開車蓋這種沒有用處而想找飯吃的人,彭更一定不會給他飯吃。即使這樣,孟子舉毀壞屋瓦、割開車蓋的例子,也是不能駁倒彭更的。為什麼呢?因為凡是目的在於想謀生的人中,毀壞屋瓦、割開車蓋的人並不包括在內。既然不包括在內,就難於用它來反駁別人了。一個人無緣無故地毀壞屋瓦、割開車蓋,這人不是傻子、瘋子,就是鬧著玩的。傻子和瘋子沒有謀生的目的,鬧著玩的人也沒有謀生的目的。想謀生的人,所做的大都是對人們共同有益的事情,他們把做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賣,得錢回來,才能有飯吃。孟子現在說的毀壞屋瓦、割開車蓋,對人沒有好處,還談得上有什麼謀生的目的呢?有頭腦的人,知道它對人沒有益處,一定不會去做;沒有頭腦的人,跟傻子、瘋子差不多,也就肯定沒有謀生的目的。其實,毀壞屋瓦,割開車蓋,跟小孩在路上玩擊壤遊戲有什麼不同呢?在路上玩擊壤遊戲的小孩,他們的目的也是想謀生嗎?他們還是小孩,沒有什麼目的可言。大人玩博戲,也屬割開車蓋之類行為。玩博戲的人,他們的目的也是為了謀生嗎?玩博戲的還有人用來相互贏取錢財,贏的錢財多了,自己也就有了飯吃,這或許是有目的的。那麼,扔石頭和跳遠的人,也屬於割開車蓋之類行為。扔石頭和跳遠的人,他們的目的是要謀生嗎?那麼孟子反駁彭更的話,不能認為完全合理。如果彭更聽信了孟子的話,那麼孟子可能被稱作是「專門靠巧言詭辯來對付人」的了。
【原文】
30·20匡章子曰(1):「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2)?居于于陵(3),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4),扶服往(5),將食之(6)。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7)!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8),則蚓而後可者也(9)。夫蚓,上食槁壤(10),下飲黃泉(11)。仲子之所居室(12),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13)?所食之粟(14),伯夷之所樹與(15),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16)?彼身織屨(17),妻辟。。(18),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19),蓋祿萬鍾(20)。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21),處于于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22),己頻蹙曰(23):『惡用是。。。。者為哉(24)?』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25),曰:『是。。。。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為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26)。」
【註釋】
(1)匡章子:姓匡,名章。齊國人。戰國時齊國將軍。齊威王時,曾擊退秦軍進攻。齊湣(m!n敏)王時,率軍在垂沙大敗楚軍,殺楚將唐昧。其言行散見於《戰國策·齊策·燕策》及《呂氏春秋·不屈》。
(2)陳仲子:又叫田仲、陳仲、於陵仲子。齊國人,戰國時齊國貴族。舊稱他是個廉潔的高士。參見33·13注(8)。
(3)於(w&污)陵:戰國時齊國地名,在今山東省鄒平縣東南。
(4)螬(c2o曹):金龜子的幼蟲。
(5)扶服:同「匍匐」,爬行。
(6)將:拿,取。
(7)巨擘(b簸):大拇指。這裡指首屈一指的人物。
(8)充:擴大。
(9)這句話的意思是,按陳仲子廉潔的標準,人世間無法做到,連他自己也沒有做到,只有成了蚯蚓才能達到。
(10)槁(g3o搞):枯乾。
(11)黃泉:指地下水。
(12)疑本句該作「仲子所居之室」。下文「所食之粟」與此對文,可一證。下文「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正以「所居之宅」與「所食之粟」對文,可二證。《孟子·滕文公下》作「所居之室」,可三證。
(13)抑:還是。
(14)粟:這裡泛指穀物,糧食。
(15)樹:種植,栽種。
(16)傷:妨礙,妨害。
(17)屨:麻鞋。
(18)辟:把麻撕開連接起來。。。(l*盧):把麻練得柔軟潔白。
(19)戴:陳戴,陳仲子的哥哥,曾做過齊國的卿。
(20)蓋(g7葛):戰國時齊國地名,陳戴的封地,在今山東省沂水縣西
(21)辟:通「避」。
(22)也:疑涉下「己」衍。
(23)頻蹙(c)促):同「顰蹙」,皺眉。
(24)。。(y@義)。。:鵝叫的聲音。
(25)《太平御覽》八六三引《論衡》文,「外」後有「來」字,可從。
(26)以上事參見《孟子·滕文公下》。
【譯文】
匡章說:「陳仲子難道不真是個廉潔的人嗎?他住在於陵,三天沒有吃東西,耳朵聽不見,眼睛看不見。井上有個李子,被金龜子的幼蟲吃去大半,他爬過去,拿來吃了。咬了三口,然後耳朵才聽得見,眼睛才看得見。」孟子說:「在齊國的人士中,我就認為陳仲子是首屈一指的!即使這樣,陳仲子怎麼能算廉潔呢?要推廣陳仲子的操行,那只有使人成為蚯蚓然後才能辦到。因為蚯蚓在地上吃乾土,在地下飲泉水。而陳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還是盜跖建造的呢?吃的糧食,是伯夷種的,還是盜跖種的呢?這是不可能知道的。」匡章說:「這有什麼關係呢!他親手編草鞋,妻子搓麻練麻,用這些來換房子和糧食。」孟子說:「陳仲子,是齊國的貴族世家,他的哥哥陳戴,在蓋地的俸祿有萬鐘。他認為哥哥的俸祿是不義的俸祿,就不肯吃;認為哥哥的房子是不義的房子,就不肯住。迴避哥哥,離開母親,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碰上有人送他哥哥一隻活著的鵝,他皺著眉說:『怎麼要這。。。。叫的東西幹什麼?』後來有一天,他母親殺了這只鵝,拿來給他吃。他哥哥正好從外邊來到家,說:『這是。。。。叫的肉。』他於是出去吐掉了。因為是母親的東西不吃,由於是妻子的東西就吃;因為是哥哥的房子不住,由於是於陵地方的房子就住。這還能算是把自己的操行推廣到所有的同類事物中去嗎?像陳仲子這樣的人,只有變成了蚯蚓,然後才能成為推廣他的操行到各個方面去的人啊。」
【原文】
30·21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1),豈為「在母不食」乎(2)?乃先譴鵝曰:「惡用。。。。者為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
【註釋】
(1)如:通「而」。
(2)「母」後疑奪一「則」字。下有「謂之『在母則不食』」,可證。
【譯文】
孟子指責陳仲子,沒有講到他的短處。陳仲子厭惡鵝肉而吐掉它,難道是因為母親做的就不吃」嗎?而是因為才剛剛譴責鵝說:「怎麼要這。。。。叫的東西幹什麼?」後來有一天他母親殺了鵝給他吃,他的哥哥說:「這是。。。。叫的肉。」陳仲子恥於違背了前面說過的話,立即把它吐了出來。要是哥哥不告訴他,他就不會吐;不吐出來,就是吃了母親做的東西。孟子說他「母親做的東西就不吃」,這不符合陳仲子的意思。假使陳仲子執意不吃母親做的東西,那麼鵝肉端上來,他就不該吃。現在既然吃了,就知道他是因為那只鵝,厭惡它而吐掉的,所以陳仲子吐掉鵝肉,是恥於吃了不符合自己志向的東西,而不是違背母子的恩情,想不吃母親做的東西。
【原文】
30·22又(1)「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2),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污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易之,正使盜之所築,己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眾,昭晰議論(3),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4),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5),耳聞目見,昭晰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6)?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7)。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8),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
【註釋】
(1)「又言」連文,本篇常見,故疑「又」下脫一「言」字。
(2)性:疑「操」之誤。上文言「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下文言「充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可證。
(3)昭晰:明晰,清楚。
(4)欲使:根據文意,疑是衍文。
(5)吐:句難通,疑誤。
(6)根據文意,疑「得」前脫一「何」字。
(7)備:周全。
(8)在:疑「充」字之誤。「充仲子之操」本篇多見,可一證。「充」與「滿」相對為文,可二證。
【譯文】
孟子又說:「陳仲子怎麼能算廉潔呢?要把他的操行推廣到各方面,那只有人變成蚯蚓之後才能辦到。蚯蚓在地上吃乾土,在地下飲泉水」。這是認為蚯蚓是最廉潔的,陳仲子要像蚯蚓一樣,才算是廉潔的。他現在住的房子,要是伯夷蓋的,吃的糧食,要是伯夷種的,這樣他去住、去吃,才能夠稱得上廉潔。或許當時吃的是盜跖種的糧食,住的是盜跖蓋的房子,那就玷污了廉潔的操行。孟子用這種觀點來指責陳仲子,也還是不正確的。房子是承襲人家舊有的,糧食是用麻鞋麻線換來的,即使房子是強盜蓋的,糧食是強盜種的,自己並沒有聽說過這些情況。如今哥哥的不義,有他自己的操行為證。操行表現在眾人面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議論紛紛,所以陳仲子才避居於陵,不住他的房子,編麻鞋搓麻線為生,不吃他的俸祿。如果陳仲子住在於陵的時候,避居像他哥哥那種人的房子,吃像他哥哥那種人的俸祿,只要他耳聞目睹,清楚無疑,那麼陳仲子不住不吃,是肯定的。現在於陵的房子沒有看見蓋的人是誰,糧食也不曉得種的人是誰,哪能有現成的房子住,哪能有現成的糧食吃呢?孟子指責他,這就太求全責備了。陳仲子住的房子,或許是強盜蓋的,他不知道而住了,就說他沒有把自己的操行推廣到各方面,只有「把自己變成蚯蚓然後才能辦到」。其實,強盜住房的地下也有蚯蚓,它吃強盜房中的乾土,飲強盜房子地下的泉水,那麼蚯蚓又怎麼能算是做到了廉潔呢?要把陳仲子的操行推廣到各方面,滿足孟子議論的要求,只有把人變成魚然後才能辦到。因為魚生活在江河海洋之中,吃的是江河海洋的泥土,而海洋不是強盜開鑿的,泥土也不是強盜堆積的。
【原文】
30·23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徒於陵歸候母也,宜自繼食而行(1)。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驕。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污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註釋】
(1)繼(j9基):攜帶。
【譯文】
但是陳仲子有個大錯誤,孟子指責他時沒有能抓住。陳仲子離開母親,避開哥哥,跟妻子單獨住在於陵,是認為哥哥的房子是不義的房子,認為哥哥的俸祿是不義的俸祿,所以才不住不吃,真是廉潔到極點。那麼他遷居於陵要回去看望母親,就該自己帶著糧食走。鵝肉端上來,一定跟飯一起。母親做的飯,是用他哥哥的祿米,母親不會自己有糧食給陳仲子吃,這是明擺著的。看來,陳仲子還是吃了他哥哥的祿米。伯夷不吃周朝的糧食,餓死在首陽山下,難道一吃周朝的糧食就會玷污他廉潔的操行嗎?陳仲子的操行,似乎不如伯夷,但孟子卻說他要變得像蚯蚓才行,這就弄錯了陳仲子的操行該拿什麼來跟他相比。
【原文】
30·24孟子曰:「莫非天命也(1),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2)。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3)非正命也(4)。」
【註釋】
(1)天:疑是衍文。《孟子·盡心上》無此文,可證。
(2)巖牆:高牆。
(3)桎:帶在腳上的刑具。梏(g)故):木製手銬。
(4)引文參見《孟子·盡心上》。
【譯文】
孟子說:「吉凶禍福沒有一樣不是命運,要順應承受它的正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要倒塌的高牆下以免死於非命。盡力行天道而死的人,是正命;戴腳鐐手銬而死的人,不是正命。」
【原文】
30·25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1)。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2),是天命於燥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3)?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4),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5),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6),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註釋】
(1)觸值之命:參見4·1注(1)。
(2)根據文意,上言「得正命」,此當其反言「得非正命」,故疑「正」下脫一「命」字。
(3)順:遵循。這裡是好的意思。
(4)戳(l)路):這裡作刑罰講。
(5)根據文意,疑「不」下脫一「噹」字。下文言「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文義正反相應,可證。
(6)子之:句子義不可通,故疑係「之子」倒誤。孔甲所入主人之子:夏朝的孔甲王,傳說有一次在東蓂山一家百姓家躲雨,正碰上女主人生孩子。有人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會富貴,有人說一定要貧賤,他說:給我當兒子,怎麼會貧賤呢?於是把孩子帶到宮中。後來這孩子因劈柴砍斷了腳,只當了個看門人。
【譯文】
孟子的話是認為人沒有「觸值之命」。遵循操行的人可得正命,胡作非為的就要得非正命,這是說天命會隨操行的好壞而變化。照這樣說,孔子沒有當帝王,顏淵早死,子夏哭瞎了眼,伯牛得麻瘋病,都是四人的操行不好嗎?為什麼都得不到正命呢?比干被挖心,伍子胥被煮死,子路被剁成肉醬,這都是天下最殘酷的刑罰,而不僅僅只是戴腳鐐手銬了。如果一定要用受刑而死來證明得到的不是正命,那麼比干、伍子胥的操行都不好了。人從天稟受了性命,有的該被壓死,有的該被淹死,有的該被殺死、有的該被燒死,即使這些人中有人謹慎地修養操行,那有什麼用處呢!竇廣國跟一百人一起躺在炭堆下,炭堆倒塌,其他一百人都死了,只有竇廣國一人得救,這是他命中注定該被封侯。炭堆與高牆有什麼兩樣?命不該被壓死,即使高牆倒塌,只要有竇廣國的命就會逃脫。「一個人幹事,像有股力量在促使他;不幹,也像有股力量在阻止他。」命該被壓死,就像有股力量促使他站在高牆下去被壓死。夏王孔甲所進的那戶人家的孩子,天命該卑賤,即使他被帶進宮中,還是做了守門的人。不站在高牆的下面,跟夏王孔甲帶那孩子進宮,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