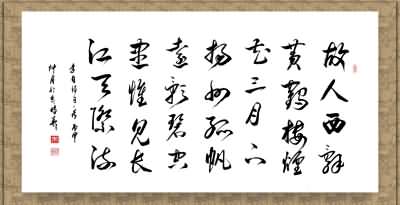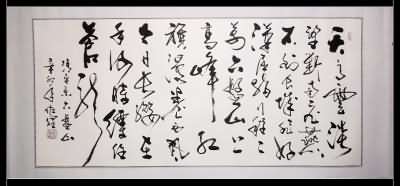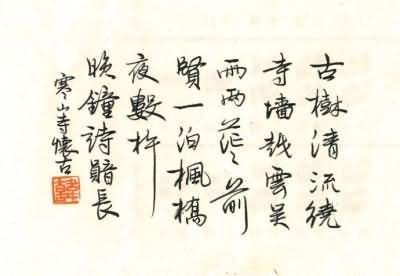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史通·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樸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核諸?「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原田是謀」,輿人【2】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而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
唯王、宋著書【3】,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余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仿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樸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而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鹹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於唐‧劉知幾《史通‧言語》)
言辭一經內心發出,就關係到榮耀和恥辱,言辭沒有文采,就不能傳佈久遠,可知修飾言辭以獨自應對,是古人所重視的。上古時候,人們都質樸簡略,當時的言語後人難以理解,須通過解釋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卻記事簡略而意義深刻,要考查文辭則言辭艱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鑒了夏、商二代的禮儀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別重視應對辭令,語言委婉而切當,言辭流暢華美而不過分。
追尋戰國以前,史書記載的言語都可以吟詠朗誦,這不是編寫時修改的結果,實在是當時言語本身質樸優美的緣故。如何來核證呢?「山木」「輔車」,就是當時民間的諺語;「原田是謀」,是普通眾人的吟詠。這些都是草野低賤之人的吟詠,尚且能如此溫潤和婉,何況身著朝服立於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當時人說出的話,被史官們載入了史冊,雖然有所加工潤色,但終究沒有失去本色。但後來的作者,普遍沒有遠見,記載當時口語,很少能如實而書,反而倣傚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時候的言辭出現於魏晉時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實,現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實與虛假由此而錯亂。
只有王劭著《齊志》、宋孝王著《關東風俗傳》,敘述西魏元氏政權、北齊高氏政權的史事,直言不諱直書其事,力求體現直筆的原則,地方口語、世俗言談,由此得以充分彰顯。而當今的學者,都責難這二人之書言辭污濁不潔淨,語言過於淺俗。其實當時語言的本質就是如此,卻把過失推給史臣,猶如照鏡子的人看到嫫母太醜,而歸罪於明鏡一樣。近來有敦煌的張太素、中山的郎余令,都以著述並稱,自恃有史學才能。郎余令著有《孝德傳》,張太素著有《隋後略》。凡所編撰當今的語言,都仿照過去的文辭。如果選擇言詞可以倣傚古代的才寫,那些難以倣傚古語記錄的,就忽略不記,可以想像,被他們所遺棄的材料,能記得完嗎?
江芊罵商臣說:「呀!賤人,難怪君王要廢了你而立職為太子。」漢王對酈食其發怒說:「小子,你幾乎壞了老子的事。」單固對楊康說:「老奴,你死得活該。」樂廣讚歎衛玠說:「這是誰家生了這樣的孩兒!」這些都是當時輕慢的語言,世俗粗野的說法。一定可以流傳於口頭,被人誦讀,但世人都認為前面兩句不失清雅,後面兩句則特別拙樸,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楚漢與今天相隔久遠,事情已成為古事;魏晉與今天年代較近,語言還類似今天。已成為久遠古事就稱它文雅,還類似今天的就驚訝於它的質樸。天地永存,風俗不會固定不變,後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寫出今天的語言,卻勇於倣傚古代的語言,豈不糊塗嗎!
善於治理國家政事的人,不選擇被治理的對象而能治好,所以風俗無論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長修史的人,不選擇事情而記載,所以語言無論美醜善惡,都能流傳至後代。如果所記載的事情都不謬誤,語言必定接近真實,幾乎就可以與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廢棄無用的事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