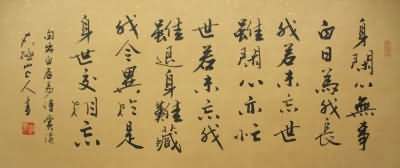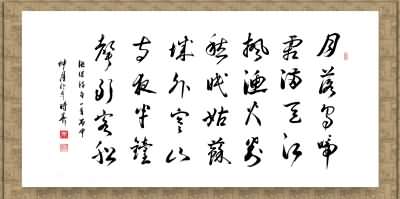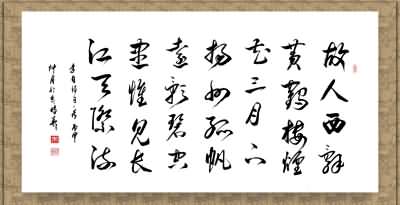楊朱第七
【原文】
楊朱游於魯1,捨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莖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2。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則己施3,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4:「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5,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6,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註釋】
1楊朱——戰國初思想家,又稱為楊子、陽子居、陽生,魏國人。主張「貴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孟子說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2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張湛註:「言不專美惡於己。」
3君盈則己降,君覽則己施——張湛註:「此推惡於君也。」
4曰——以下仍為楊朱之言。
5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楊伯峻:「堯以天下讓許由,事又見《莊子·逍遙游篇》。舜讓天下於善卷,亦見《莊子·逍遙游篇》及《盜跖篇》。」
6孤竹君——楊伯峻:「《御覽》四二四、《類聚》二十一引並無『君』字,是也。」
【譯文】
楊朱到魯國遊覽,住在孟氏家中。孟氏問他:「做人就是了,為什麼要名聲呢?」楊朱回答說:「要以名聲去發財。」孟氏又問:「已經富了,為什麼還不停止呢?」楊朱說:「為做官。」孟氏又問:「已經做官了,為什麼還不停止呢?」楊朱說:「為了死後喪事的榮耀。」孟氏又問:「已經死了,還為什麼呢?」楊朱說:「為子孫。」孟氏又問:「名聲對子孫有什麼好處?」楊朱說:「名聲是身體辛苦、心念焦慮才能得到的。伴隨著名聲而來的,好處可以及於宗族,利益可以遍施鄉里,又何況子孫呢?」孟氏說:「凡是追求名聲的人必須廉潔,廉潔就會貧窮;凡是追求名聲的人必須謙讓,謙讓就會低賤。」楊朱說:「管仲當齊國宰相的時候,國君淫亂,他也淫亂;國君奢侈,他也奢侈。意志與國君相合,言論被國君聽從,治國之道順利實行,齊國在諸侯中成為霸主。死了以後,管仲還是管仲。田氏當齊國宰相的時候,國君富有,他便貧苦;國君搜括,他便施捨。老百姓都歸向於他,他因而佔有了齊國,子子孫孫享受,至今沒有斷絕。像這樣,真實的名聲會貧窮,虛假的名聲會富貴。」楊朱又說:「有實事的沒有名聲,有名聲的沒有實事。名聲這東西,實際上是虛偽的。過去堯舜虛偽地把天下讓給許由、善卷,而實際上並沒有失去天下,享受帝位達百年之久。伯夷、叔齊真實地把孤竹國君位讓了出來而終於失掉了國家,餓死在首陽山上。真實與虛偽的區
別,就像這樣明白。」
【原文】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1。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2,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3,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4,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爾順耳目之觀聽5,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住,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6,故不為名所勸7;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註釋】
1齊——定限。
2弭——除去。
3■然——音you(由),舒適自得貌。介——微小。
4厭——通「饜」,吃飽,引申為滿足。
5■■——獨行貌。順——《集釋》:「『順』,《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元本、世德堂本並作『慎』。《意林》引同。」順通慎。
6當身——俞樾:「『當身』乃『當生』之誤。下雲,『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雲,『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7勸——《集釋》:「北宋本、汪本、《四解》本『勸』作『觀』,今依吉府本、《道藏》白文本、世德堂本正。」
【譯文】
楊朱說:「一百歲,是壽命的極限。能活到一百歲的,一千人中難有一人。即使有一人,他在孩童與衰老糊塗的時間,幾乎佔去了一半時間。再去掉夜間睡眠的時間,去掉白天休息的時間,又幾乎佔去了一半。加上疾病痛苦、失意憂愁,又幾乎佔去了一半。估計剩下的十多年中,舒適自得,沒有絲毫顧慮的時間,也沒有其中的一半。那麼人生在世又為了什麼呢?有什麼快樂呢?為了味美豐富的食物吧,為了悅耳的音樂與悅目的女色吧,可是味美豐富的食物並不能經常得到滿足,悅耳的音樂與悅目的女色也不能經常聽得到與玩得到。再加上要被刑罰所禁止,被賞賜所規勸,被名譽所推進,被法網所阻遏,惶恐不安地去競爭一時的虛偽聲譽,以圖死後所留下的榮耀,孤獨謹慎地去選擇耳朵可以聽的東西與眼睛可以看的東西,愛惜身體與意念的是與非,白白地喪失了當時最高的快樂,不能自由自在地活一段時間,這與罪惡深重的囚犯所關押的一層又一層的牢籠又有什麼區別呢?上古的人懂得出生是暫時的到來,懂得死亡是暫時的離去,因而隨心所欲地行動,不違背自然的喜好,不減少今生的娛樂,所以不被名譽所規勸,順從自然本性去遊玩,不違背萬物的喜好,不博取死後的名譽,所以不被刑罰所牽連。名譽的先後,壽命的長短,都不是他們所考慮的。」
【原文】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
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
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1。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2。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逢死後?」
【註釋】
1賤非所賤——張湛註:「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楊伯峻:「『故生非所生』諸『所』字下疑皆脫『能』字。此數語緊承『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能也』而言。細繹張注及下文盧解,似其所見本俱有『能』字。」
2齊貴齊賤——張湛註:「皆同歸於自然。」盧重玄解:「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
【譯文】
楊朱說:「萬物所不同的是生存,所相同的是死亡。生存就有賢有愚、有貴有賤,這是不同的;死亡就有腐爛發臭、消失滅亡,這是相同的。即使是這樣,賢愚與貴賤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腐臭、消滅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所以生不是人所能生,死不是人所能死,賢不是人所能賢,愚不是人所能愚,貴不是人所能貴,賤也不是人所能賤,然而萬物的生與死是一樣的,賢與愚是一樣的,貴與賤也是一樣的。活十年也是死,活百年也是死。仁人聖人也是死,凶人愚人也是死。活著是堯舜,死了便是腐骨;活著是桀紂,死了也是腐骨。腐骨是一樣的,誰知道它們的差異呢?姑且追求今生,哪有工夫顧及死後?」
【原文】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1,以放餓死2。展季非亡情3,矜貞之郵,以放寡宗4。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註釋】
1矜清之郵——矜,顧惜。清,清白。郵,通「尤」,最。介夷過於清白,指周武王滅商後,伯夷恥之,誓不食周粟,至餓死於首陽山之事。
2放——音 fǎng(訪),至。
3展季非亡情——展季,即展禽,名獲,字季,又稱柳下惠,春秋時魯國人,仕為士師,為人正直,不阿諛奉承。
4寡宗——宗,宗族。寡宗,指宗族後代很少。
【譯文】
楊朱說:「伯夷不是沒有慾望,但過於顧惜清白的名聲,以至於餓死了。展季不是沒有人情,但過於顧惜正直的名聲,以至於宗人稀少。清白與正直的失誤就像他們兩人這樣。」
【原文】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1,子貢殖於衛2。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註釋】
1原憲窶於魯——原憲,春秋時魯國人,一說為宋國人,字子思,亦稱
原思,孔子弟子,性狷介,住草棚,穿破衣,子貢曾嘲笑他。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窶,音 ju(據),張湛註:「貧也。」
2子貢殖於衛——子貢,姓端末,名賜,字子貢,孔子弟子,衛國人。殖,指貨殖,經商。
【譯文】
楊朱說:「原憲在魯國十分貧窮,子貢在衛國經商掙錢。原憲的貧窮損害了生命,子貢的經商累壞了身體。」「那麼貧窮也不行,經商也不行,怎樣才行呢?」答:「正確的辦法在於使生活快樂,正確的辦法在於使身體安逸。所以善於使生活快樂的人不會貧窮,善於使身體安逸的人不去經商。」
【原文】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難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1,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2。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3。』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4,而不得嗅,謂之閼顫5;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行,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6。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7,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捨8,慼慼然以至久生9,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十,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註釋】
1犧牲——古代祭祀所用牲畜的通稱。
2晏平仲——即晏嬰,字平仲,春秋時齊國大夫。
3閼——音 e(厄),阻塞。
4椒蘭——花椒和蘭草,都很香。
5顫——張湛註:「鼻通曰顫。」
6廢虐——張湛註:「廢,大也。」《釋文》:「廢虐,毀殘也。」
7熙熙然——《釋文》:「縱情慾也。」
8錄——檢束。
9慼慼然——憂懼貌。
十瘞——音y(意),埋葬。
i
■袞衣——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禮眼。槨——棺外的套棺。
【譯文】
楊朱說:「古代有句話說:『活著的時候互相憐愛,死了便互相拋棄。』這句話說到底了。互相憐愛的方法,不僅僅在於感情,過於勤苦的,能使他安逸,飢餓了能使他吃飽,寒冷了能使他溫暖,窮困了能使他順利。互相拋棄的方法,並不是不互相悲哀,而是口中不含珍珠美玉,身上不穿文彩繡衣,
祭奠不設犧牲食品,埋葬不擺冥間器具。晏嬰向管仲詢問養生之道。管仲說:『放縱罷了,不要壅塞,不要阻擋。』晏嬰問:『具體事項是什麼?』管仲說:『耳朵想聽什麼就聽什麼,眼睛想看什麼就看什麼,鼻子想聞什麼就聞什麼,嘴巴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身體想怎麼舒服就怎麼舒服,意念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耳朵所想聽的是悅耳的聲音,卻聽不到,就叫做阻塞耳聰;眼睛所想見的是漂亮的顏色,卻看不到,就叫做阻塞目明;鼻子所想聞的是花椒與蘭草,卻聞不到,就叫做阻塞嗅覺;嘴巴所想說的是誰是誰非,卻不能說,就叫做阻塞智慧;身體所想舒服的是美麗與厚實,卻得不到,就叫做抑制舒適;意念所想做的是放縱安逸,卻做不到,就叫做抑制本性。凡此種種阻塞,都是殘毀自己的根源,清除殘毀自己的根源,放縱情慾一直到死,即使只有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這就是我所說的養生。留住殘毀自己的根源,檢束而不放棄,憂懼煩惱一直到老,即使有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也不是我所說的養生。』管仲又說:『我已經告訴你怎樣養生了,送死又該怎樣呢?』晏嬰說:『送死就簡單了,我怎麼跟你說呢?』管仲說:『我就是想聽聽。』晏嬰說:『已經死了,難道能由我嗎?燒成灰也行,沉下水也行,埋入土中也行,露在外面也行,包上柴草扔到溝壑裡也行,穿上禮服繡衣放入棺槨裡也行,碰上什麼都行。』管仲回頭對鮑叔黃子說:『養生與送死的方法,我們兩人已經說盡了。』」
【原文】
子產相鄭1,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曲成封2,望門百步3,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4,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者以盈之5。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暱,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6,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7。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8。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9!」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十,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欲,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腎海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誇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註釋】
1子產——即公孫僑、公孫成子,春秋時政治家,鄭貴族子國之子,名僑,字子產,鄭簡公十二年(前 554 年)為卿,二十三年(前 543 年)執政。
2積曲成封——曲,酒麴,釀酒的發酵劑。封,土堆。
3望——楊伯峻:「《廣雅·釋詁》云:望,至也。」
4悔吝——悔恨。
5稚齒■■——稚齒,年少。■■,音wǒ(我)tuǒ(妥),美好貌,指女子。
6娥姣——美好,指女子。
7弗獲——楊伯峻:「『弗』字疑衍,或者為『必』字之誤。」
8造——往,到。
9詔——告,多用於上告下,本文是謙同。
十將——秉承。
■喻之——楊伯峻:「『喻之,當作『喻若』。」
■忙然——即茫然,失意貌。
【譯文】
子產任鄭國的宰相,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三年之後,好人服從他的教化,壞人害怕他的禁令,鄭國得到了治理,各國諸侯都害怕鄭國。他有個哥哥叫公孫朝,有個弟弟叫公孫穆。公孫朝嗜好飲酒,公孫穆嗜好女色。公孫朝的家裡,收藏的酒達一千壇,積蓄的酒麴堆成山,離他家大門還有一百步遠,酒糟的氣味便撲鼻而來。在他被酒菜荒廢的日子裡,不知道時局的安危,人理的悔恨,家業的有無,親族的遠近,生死的哀樂,即使是水火兵刃一齊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公孫穆的後院並列著幾十個房間,裡面都放著挑選來的年輕美貌的女子。在他沉湎於女色的日子裡,排除一切親戚,斷絕所有的朋友,躲到了後院裡,日以繼夜,三個月才出來一次,還覺得不愜意。發現鄉間有美貌的處女,一定要用錢財把她弄來,托人做媒並引誘她,必須到了手才罷休。子產日夜為他倆憂愁,悄悄地到鄧析那裡討論辦法,說:「我聽說修養好自身然後推及家庭,治理好家庭然後推及國家,這是說從近處開始,然後推廣到遠處。我治理鄭國已經成功了,而家庭卻混亂了。是我的方法錯了嗎?有什麼辦法挽救我這兩個兄弟呢?請你告訴我。」鄧析說:「我已經奇怪很久了,沒敢先說出來,你為何不在他們清醒的時候,用性命的重要去曉喻他們,用禮義的尊貴去誘導他們呢?」子產採用了鄧析的話,找了個機會去見他的兩位兄弟,告訴他們說:「人比禽獸尊貴的地方,在於人有智慧思慮。智慧思慮所依據的是禮義。成就了禮義,那麼名譽和地位也就來了。你們放縱情慾去做事,沉溺於嗜欲,那麼性命就危險了。你們聽我的話,早上悔改,晚上就會得到俸祿了。」公孫朝和公孫穆說:「我懂得這些已經很久了,做這樣的選擇也已經很久了,難道要等你講了以後我們才懂得嗎?生存難得碰上,死亡卻容易到來。以難得的生存去等待容易到來的死亡,還有什麼可考慮的呢?你想尊重禮義以便向人誇耀,抑制本性以招來名譽,我以為這還不如死了好。為了要享盡一生的歡娛,受盡人生的樂趣,只怕肚子破了不能放肆地去喝酒,精力疲憊了不能放肆地去淫樂,沒有工夫去擔憂名聲的醜惡和性命的危險。而且你以治理國家的才能向我們誇耀,想用漂亮的詞句來擾亂我們的心念,用榮華富貴來引誘我們改變意志,不也鄙陋而可憐嗎?我們又要和你辨別一下。善於治理身外之物的,外物未必能治好,而自身卻有許多辛苦;善於治理身內心性的,外物未必混亂,而本性卻十分安逸。以
你對身外之物的治理,那些方法可以暫時在一個國家實行,但並不符合人的本心;以我們對身內心性的治理,這些方法可以推廣到天下,君臣之道也就用不著了。我們經常想用這種辦法去開導你,你卻反而要用你那辦法來教育我們嗎?」子產茫然無話可說。過了些天,他把這事告訴了鄧析。鄧析說:「你同真人住在一起卻不知道他們,誰說你是聰明人啊?鄭國的治理不過是偶然的,並不是你的功勞。」
【原文】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1。藉其先貨,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台樹,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2,非齊土之所產育者3,無不必致之4,猶藩牆之物也5。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逞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6,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7。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干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8,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9,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厘聞之十,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註釋】
1世——後嗣。
2殊方偏國——殊方,異域他鄉。偏國,邊遠國家。
3齊土——中土,指中原地區。
4無不必致之——俞樾:「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5藩牆——藩,籬笆。藩牆,猶藩籬,圍牆。
6住——俞樾:「『住』當為『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
7廡——音wǔ(武),堂周的廊屋。
8媵——音yng(映),隨嫁的人。
i
9賦而藏之——俞樾:「賦者,計口出錢也。」「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得相通。」
十禽骨厘——又作禽滑厘、禽屈厘,戰國初人,墨子弟子。
■段於生——王重民:「《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段干生』作『段干木』,當從之。」段干木,戰國初魏國人。
【譯文】
衛國的端木叔,是子貢的後代。依靠他祖先的產業,家產達萬金。不再從事世俗雜務,放縱意念去追求享受。凡是活著的人所想做的,人們心中所想玩的,他沒有不去做,沒有不去玩的。高牆大院,歌台舞榭,花園獸囿,魚池草沼,甘飲美食,華車麗服,美聲妙樂,嬌妻艷妾,可以與齊國和楚國的國君相比擬。至於他的情慾所喜好的,耳朵所想聽的,眼睛所想看的,嘴巴所想嘗的,即使在遙遠的地方、偏僻的國家,不是中原所生產養育的,沒
有搞不到手的東西,就像拿自己圍牆內的東西一樣。至於他出去遊覽,即使山河阻險,路途遙遠,沒有走不到的地方,就像一般人走幾步路一樣。庭院中的賓客每天以百計,廚房裡的煙火一直不斷,廳堂裡的音樂一直不絕。自奉自養之後剩下來的東西,先施捨給本宗族的人,施捨本宗族剩下來的東西,再施捨給本邑里的人,施捨本邑里剩下來的東西,才施捨給全國的人。到了六十歲的時候,血氣軀幹都將衰弱了,於是拋棄家內雜事,把他的全部庫藏及珍珠寶玉、車馬衣物、少婦美女,在一年之中全部散盡,沒有給子孫留一點錢財。等到他生病的時候,家中沒有一點藥物;等到他死亡的時候,家中沒有一點埋葬用的錢財。一國之中受過他施捨的人,共同出錢埋葬了他,並把錢財都還給了他的子孫。禽骨厘聽到了這件事,說:「端木叔是個瘋狂的人,侮辱了他的祖先了。」段干生聽到了這件事,說:「端木叔是個通達的人,德行超過他的祖先了。他的行動,他的作為,一般人覺得驚訝,卻符合真實的情理。衛國的君子們多以禮教自我約束,本來就是不可理解端木叔這個人的本心的。」
【原文】
孟孫陽問楊朱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1,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2,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3,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4。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註釋】
1蘄——能「祈」,祈求。
2更——經歷。
3廢而任之——放棄努力,聽之任之。
4放——音 fǎng(訪),至。
【譯文】
孟孫陽問楊朱說:「這裡有個人,尊貴生命,愛惜身體,以求不死,可以嗎?」楊朱說:「沒有不死的道理。」孟孫陽又問:「以求長壽,可以嗎?」楊朱說:「沒有長壽的道理。生命並不因為尊貴它就能存在,身體並不因為愛惜它就能壯實。而且長久活著幹什麼呢?人的情慾好惡,古代與現在一樣;身體四肢的安危,古代與現在一樣;人間雜事的苦樂,古代與現代一樣;朝代的變遷治亂,古代與現在一樣。已經聽到了,已經看到了,已經經歷了,活一百年還嫌太多,又何況長久活著的苦惱呢?」孟孫陽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早點死亡就比長久活著更好,那麼踩劍鋒刀刃,入沸水大火,就是滿足願望了。」楊子說:「不是這樣的。已經出生了,就應當聽之任之,心念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一直到死亡。將要死亡了,就應當聽之任之,屍體該放到哪裡就到哪裡,一直到消失。一切都放棄努力,一切都聽之任之,何必在人間考慮早死與晚死呢?」
【原文】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捨國而隱耕。
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1。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2;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3。」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註釋】
1偏枯——一般指半身不遂,本文指勞累成疾。
2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張湛註:「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3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張湛註:「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譯文】
楊朱說:「伯成子高不肯用一根毫毛去為他人謀利益,拋棄了國家,隱居種田去了。大禹不願意以自己的身體為自己謀利益,結果全身殘疾。古時候的人要損害一根毫毛去為天下謀利益,他不肯給;把天下的財物都用來奉養自己的身體,他也不願要。人人都不損害自己的一根毫毛,入人都不為天下人謀利益,天下就太平了。」禽子問楊朱說:「取你身上一根汗毛以救濟天下,你幹嗎?」楊子說:「天下本來不是一根汗毛所能救濟的。」禽子說:「假使能救濟的話,幹嗎?」楊子不吭聲。禽子出來告訴了盂孫陽。孟孫陽說:「你不明白先生的心,請讓我來說說吧。有人侵犯你的肌肉皮膚便可得到一萬金,你幹嗎?」禽子說:「干。」孟孫陽說:「有人砍斷你的一節身體便可得到一個國家,你幹嗎?」禽子沉默了很久。孟孫陽說:「一根汗毛比肌肉皮膚小得多,肌肉皮膚比一節身體小得多,這十分明白。然而把一根根汗毛積累起來便成為肌肉皮膚,把一塊塊肌肉皮膚積累起來便成為一節身體。一根汗毛本是整個身體中的萬分之一部分,為什麼要輕視它呢?」禽子說:「我不能用更多的道理來說服你。但是用你的話去問老聃、關尹,那你的話就是對的了;用我話去問大禹、墨翟,那我的話就是對的了。」孟孫陽於是回頭同他的學生說別的事去了。
【原文】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1,禪位於禹,慼慼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2。■治水土3,績用不就,殛諸羽山4。禹纂業事仇5,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6。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7,慼慼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8,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9,僅免其身,慼慼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
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十,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慼慼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慾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註釋】
1商鈞——又作商均,舜之子。
2天人——天子。窮毒——困窮苦毒。
3■——同鯀,傳說為禹的父親,因治水未成,被舜殺死在羽山。4殛——音 j(極),誅戮。
i
5纂業事仇——纂,通「纘」,音 zuān,繼承。仇,指殺父之仇人,即舜。
6胼胝——音 pian(駢)zhī(支),老繭。
7紱冕——音 fu(弗)miǎn(免)。紱為古代作祭服的蔽膝,冕為古代帝王的禮帽,這裡泛指祭服。
8邵公不悅——《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又《史記·周本紀》:「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列子》所記與此不完全相同。
9誅兄放弟——誅,殺。放,流放。《史記》雲誅管叔,放蔡叔。
十伐樹於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削跡於衛——《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不久,有人在靈公前說孔子壞話,靈公便派兵仗在孔子住宅中出入,以威脅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日,去衛。」其後一度被用,但「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又離開了衛國。
■窮於商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由衛適陳,過匡,因孔子狀似陽虎,匡人以為陽虎至,遂拘孔子。商周不知在何處。
■圍於陳蔡——《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欲往,陳蔡大夫便派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季氏——即季孫氏,春秋、戰國時魯國掌握政權的貴族,魯桓公少子季友的後裔。
■陽虎——魯國季氏家臣,事季平子。
■天民——有道之民。但後面的天民又指天子。遑遽——驚懼慌張。
■雖稱之弗知——俞樾:「上文言舜、禹、周、孔曰:『雖稱之弗知,
雖賞之不知。』則此言桀、紂,宜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不知。』『毀之』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所歸,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是美之所歸也,『毀之罰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譯文】
楊朱說:「天的美名歸於舜、禹、周公、孔子,天下的惡名歸於夏桀、商紂。但是舜在河陽種莊稼,在雷澤燒陶器,四肢得不到片刻休息,口腹得不到美味飯菜,父母不喜歡他,弟妹不親近他,年齡到了三十歲,才不得不先報告父母就娶妻。等到接受堯的禪讓時,年齡已經太大了,智力也衰弱了。兒子商鈞又無能,只好把帝位讓給禹,憂鬱地一直到死。這是天子中窮困苦毒的人。■治理水土,沒有取得成績,被殺死在羽山。禹繼承他的事業,給殺父的仇人做事,只怕荒廢了治理水土的時間,兒子出生後沒有時間給他起名字,路過家門也不能進去,身體惟悴,手腳都生了繭子。等到他接受舜讓給他的帝位時,把宮室蓋得十分簡陋,卻把祭祀的禮眼做得很講究,憂愁地一直到死。這是天子中憂愁辛苦的人。武王已經去世,成王還很年幼,周公行使天子的權力。邵公不高興,幾個國家流傳著謠言。周公到東方居住了三年,殺死了哥哥,流放了弟弟,自己才保住了生命,憂愁地一直到死。這是天子中危險恐懼的人。孔子懂得帝王治國的方法,接受當時各國國君的邀請,在宋國時曾休息過的大樹被人砍伐,在衛國時一度做官卻又被冷落,在商周時被拘留監禁,在陳國與蔡國之間被包圍絕糧,又被季氏輕視,被陽虎侮辱,憂愁地一直到死。這是有道賢人中驚懼慌張的人。所有這四位聖人,活著的時候沒有享受一天的歡樂,死了後卻有流傳萬代的名聲。死後的名聲本來不是實際生活所需要的,即使稱讚自己也不知道,即使獎賞自己也不知道,與樹樁土塊沒有什麼差別了。夏粱憑借歷代祖先的資本,佔據著天子的尊貴地位,智慧足以抗拒眾臣,威勢足以震動海內;放縱耳國所想要的娛樂,做盡意念想做的事情,高高興興地一直到死。這是天子中安逸放蕩的人。商紂也憑借歷代祖先的資本,佔據著天子的尊貴地位,威勢沒有任何地方行不通,意志沒有任何人不服從,在所有的宮殿中肆意淫亂,在整個黑夜裡放縱情慾,不用禮義來使自己困苦,高高興興地一直到被殺。這是天子中放肆縱慾的人。這二個兇惡的人,活著時有放縱慾望的歡樂,死了後蒙上了愚頑暴虐的壞名聲。實際生活本來不是死後的名聲所能相比的,即使譭謗他也不知道,即使懲罰他也不知道,這與樹樁土塊有什麼不同呢?那四位聖人雖然都得到了美名,但辛辛苦苦一直到最後,都歸於死亡了。那兩個兇惡的人雖然都得到了惡名,但高高興興一直到最後,也都歸於死亡了。」
【原文】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1,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2,使五尺童子荷■而隨之3,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4。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5。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註釋】
1芸——通「耘」,除草。
2而群——王重民:「《類聚》九十四引上『而』字作『為』,疑作『為』者是也。」王叔岷:「《御覽》八三三、《事文類聚·後集》二九、《中天記》五四引『而群』亦並作『為群』,王說是也。」
3荷■——荷,著 he(賀),扛,拿。,即棰,鞭子。
4其極遠也——王叔岷:「《說苑·政理篇》、《金樓子·立言下篇》『其』下並有『志』字,當從之。下文『何則?其音疏也,』『志』勻『音』對言。」
5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黃鐘、大呂,古代音律十二律中的前二律,這裡作為十二律的代稱。十二律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奏,陶鴻慶云:「『奏』當為『湊』。湊,會合也。」
【譯文】
楊朱進見梁王,說治理天下就同在手掌上玩東西一樣容易。梁王說:「先生有一妻一妾都管不好,三畝大的菜園都除不淨草,卻說治理天下就同在手掌上玩東西一樣容易,為什麼呢?」楊朱答道:「您見到過那牧羊的人嗎?成百隻羊合為一群,讓一個五尺高的小孩拿著鞭子跟著羊群,想叫羊向東羊就向東,想叫羊向西羊就向西。如果堯牽著一隻羊,舜拿著鞭子踉著羊,羊就不容易往前走了。而且我聽說過:能吞沒船隻的大魚不到支流中遊玩,鴻鵲在高空飛翔不落在池塘上。為什麼?它們的志向極其遠大。黃鐘大呂這樣的音樂不能給煩雜湊合起來的舞蹈伴奏。為什麼?它們的音律很有條理。準備做大事的不做小事,要成就大事的不成就小事,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原文】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譯文】
楊朱說:「太古的事情已經完全消滅了,誰把它記載下來的呢?三皇的事跡好像有,又好像沒有;五帝的事跡好像明白,又好像在夢中;三王的事跡有的隱藏了,有的顯示出來,一憶件事中未必知道一件。當世的事情有的聽說了,有的看見了,一萬件中未必明瞭一件。眼前的事情有的存在著,有的過去了,一千件中未必明瞭一件。從太古直到今天,年數固然計算不清,但自伏羲以來三十多萬年,賢人與愚人,好人與壞人,成功的事情與失敗的事情,對的事情與錯的事情,沒有不消滅的,只是早晚快慢不同罷了。顧惜一時的譭謗與讚譽,使自己的精神與形體焦的痛苦,求得死後幾百年中留下的名聲,怎麼能潤澤枯槁的屍骨?這樣活著又有什麼樂趣呢?」
【原文】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1,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御,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2,無毛羽以御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3,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4。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5,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之物者6,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註釋】
1人肖天地之類——張湛註:「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五行,木火土金水。
2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趨走,《釋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從利逃害,《集釋》:「本作『逃利害』,今從敦煌斯七七七六朝寫本訂正。」
3以為養——《集釋》:「各本『養』下有『性』字,今從敦煌斯七七七六朝寫本殘卷刪。」
4不得而去之——《集釋》:「北宋本、汪本、秦刻盧解本、世德堂本留作『不得不去之』。俞樾曰:當作『不得而去之』。……俞說是也。《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吉府本正作『而』,今訂正。」
5雖全生——《集釋》:「各本『生』下有『身』字,今從敦煌斯七七七六朝殘卷刪。」
6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之物——《集釋》:「各本無此十四字,今從敦煌殘卷增。」
【譯文】
楊朱說:「人與天地近似一類,懷有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本性,是生物中最有靈性的。但是人啊,指甲牙齒不能很好地守衛自己,肌肉皮膚不能很好地捍御自己,快步奔跑不能很好地得到利益與逃避禍害,沒有羽毛來抵抗寒冷與暑熱,一定要利用外物來養活自己,運用智慧而不依仗力量,所以智慧之所以可貴,以能保存自己為貴;力量之所以低賤,以能侵害外物為賤。然而身體不是我所有的,既然出生了,便不能不保全它;外物也不是我所有的,既然存在著,便不能拋棄它。身體固然是生命的主要因素,但外物也是保養身體的主要因素。雖然要保全生命,卻不可以佔有自己的身體;雖然不能拋棄外物,卻不可以佔有那些外物。佔有那些外物,佔有自己的身體,就是蠻橫地把天下的身體屬於己有,蠻橫地把天下之物屬於己有。不蠻橫地把天下的身體屬於己有,不蠻橫地把天下之物屬於己有的,大概只有聖人吧!把天下的身體歸公共所有,把天下的外物歸公共所有,大概只有至人吧!這就叫做最崇高最偉大的人。」
【原文】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民也1。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慾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2,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急3,一朝處以柔毛綈幕4,薦以梁肉蘭橘5,心■體煩6,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7,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
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8,僅以過冬。暨春東作9,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室十,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裡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註釋】
1遁民——《集釋》:「『民』本作『人』,敦煌殘卷作『民』。」王重民:「『人』應作『民』,宋本未回改唐諱。」楊伯峻:「王說是,今從之改正。」2啜菽茹藿——菽,豆類。茹,吃。藿,豆葉。
3■急——■,同「■」,音 ku(喟)。急,緊縮。
i
4綈——絲織物的一種。
5梁肉蘭橘——梁,通「粱」。梁肉,指精美的膳食。蘭橘——香美的橘子,這裡指香美的水果。
6■——音yuān(淵),憂鬱。
7商——指春秋時的宋國,為商代的後裔,故稱。侔地——侔,相等,侔地,同等地種地。
8■■——音yun(韻)fen(墳),麻絮衣。
9東作——古代五行學說以東方為木,為春,東作即春天農作。十■——音yu(遇),又讀 ao(奧),深。
■綿纊——綿,絲綿。纊,音 kuang(礦),亦作「■」,絮衣服用的新絲棉。綿纊,指絲棉■。
■戎菽——胡豆。■■莖萍子——■,音 x(徙),即麻。芹,小芹菜。
i萍子,蒿子,有青蒿、白蒿數種。
■鄉豪張湛註:「鄉豪,裡之貴者。」
【譯文】
楊朱說:「百姓們得不到休息,是為了四件事的緣故:一是為了長壽,二是為了名聲,三是為了地位,四是為了財貨。有了這四件事,便害怕鬼神,害怕別人,害怕威勢,害怕刑罰,這叫做逃避自然的人。這種人可以被殺死,可以活下去,控制生命的力量在自身之外。不違背天命,為什麼要羨慕長壽?不重視尊貴,為什麼要羨慕名聲?不求取權勢,為什麼要羨慕地位?不貪求富裕,為什麼要羨慕財貨?這叫做順應自然的人。這種人天下沒有敵手,控制生命的力量在自身之內。所以俗話說:『人不結婚做官,情慾便丟掉一半;人不穿衣吃飯,君臣之道便會消失。』周都的諺語說:『老衣可以叫做坐在那裡死去。』早晨外出,夜晚回家,自己認為這是正常的本性;喝豆汁吃豆葉,自己認為這是最好的飲食;肌肉又粗又壯,筋骨關節緊縮彎曲,一旦讓他穿上柔軟的毛裘和光潤的綢綈,吃上細糧魚肉與香美的水果,就會心憂體煩,內熱生病了。如果宋國和魯國的國君與老農同樣種地,那不到一會兒也就疲憊了。所以田野裡的人覺得安逸的,田野裡的人覺得香美的,便說是天下沒有比這更好的了。過去宋國有個農夫,經常穿亂麻絮的衣服,並只用它來過冬。到了春天耕種的時候,自己在太陽下曝曬,不知道天下還有大廈深宮,絲棉與狐貉皮裘。回頭對他的妻子說:『曬太陽的暖和,准也不知道,把它告訴我的國君,一定會得到重賞。』鄉里的富人告訴他說:『過去有以胡豆、麻桿、水芹與蒿子為甘美食物的人,對本鄉富豪稱讚它們,本鄉富豪拿來嘗了嘗,就像毒蟲叮刺了嘴巴,肚子也疼痛起來,大家都譏笑並埋怨那
個人,那人也大為慚愧。你呀,就是這樣一類人。』」
【原文】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1。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刊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3。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繫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註釋】
1蠹——音 du(妒),蛀蟲。
2悠悠者——憂愁、憂傷的人。
【譯文】
楊朱說:「高大的房屋,華麗的衣服,甘美的食物,漂亮的女子,有了這四樣,又何必再追求另外的東西?有了這些還要另外追求的,是貪得無厭的人性。貪得無厭的人性,是陰陽之氣的蛀蟲。忠並不能使君主安逸,恰恰能使他的身體遭受危險;義並不能使別人得到利益,恰恰能使他的生命遭到損害。使君上安逸不來源於忠,那麼忠的概念就消失了;使別人得利不來源於義,那麼義的概念就斷絕了。君主與臣下都十分安逸,別人與自己都得到利益,這是古代的行為準則。鬻子說:『不要名聲的人沒有憂愁。』老子說:『名聲是實際的賓客。』但那些憂愁的人總是追求名聲而不曾停止,難道名聲本來就不能不要,名聲本來就不能作賓客嗎?現在有名聲的人就尊貴榮耀,沒有名聲的人就卑賤屈辱。尊貴榮耀便安逸快樂,卑賤屈辱便憂愁苦惱。憂愁苦惱是違反本性的,安逸快樂是順應本性的。這些與實際又緊密相關。名聲怎麼能不要?名聲怎麼能作賓客?只是擔心為了堅守名聲而損害了實際啊!堅守名聲而損害了實際,所擔憂的是連危險滅亡都挽救不了,難道僅僅是在安逸快樂與優愁苦惱這二者之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