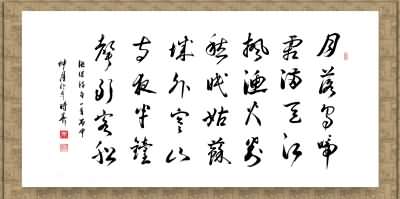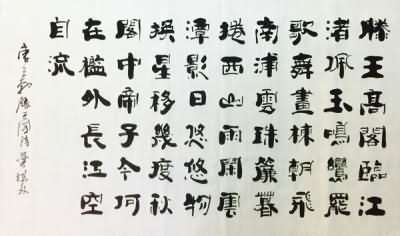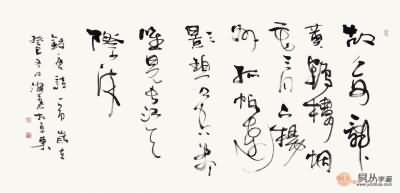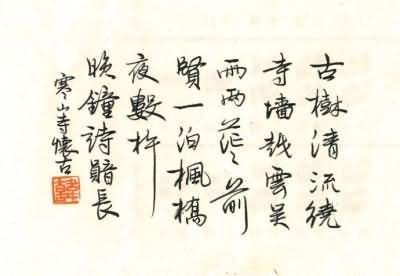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閆敬立為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萊蕪鯁澀。即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即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尚生荊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館所由("由"原作"用",據明抄本改。)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由。("由"原作"用",據明抄本改。)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俶同餐,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俶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俶又具饌,亦如法。俶處分知遠,以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卻回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馱。("被馱"明抄本作"乘之"。)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才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卻回百餘步置路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頹毀。"敬立卻回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廠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腳木馬,門前廢堠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杇爛氣。如黃衣曲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出《博異記》)
【譯文】
興元元年,朱泚作亂長安。閆敬立作段秀實的告密使,秘密離開鳳翔山,夜晚要到達太平館。那館已遷移了十里,舊館無人已很久。敬立誤入舊館,只是驚奇荒蕪枯澀。有兩個穿黑衣服的人迎門行拜,控制馬轡到大廳,就問此館因為什麼寂寞到如此地步。穿黑衣人回答說:"也可以住。"坐後,一切都遵照館驛的禮數進行著。過了一會兒,黑衣人通報說:"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到。"敬立接見他。問道:"這館很荒蕪,為什麼?"回答說:"現在天下草木叢雜,不單單這個驛館,宮殿還生荊棘呢。"敬立認為他的話奇特,談論在一般人之上。叔說"此館所用的人都已逃走。"指著兩個穿黑衣人說:"這都是我家的崑崙奴,一個叫道奴,一個叫知遠,暫且來侍奉你。"敬立於是在燈燭下,細看那奴僕,黑衫下都穿著紫白衣服,面上都有崑崙,再加上用白字印面上很分明,確實是劉俶家的人。讓看廚房,有幾個女僕陳設食具,很忙,確實沒有其他的人。過了很久,筵席擺上,食物精美。敬立和劉俶一起進餐,很飽。僕人等也都如此,才睡覺。敬立問俶道:"由於加倍兼程,馬累得很瘦,能另外借一匹馬嗎?"回答說:"小事罷了。"到了四更天,敬立命令整理車馬準備出發。劉俶又準備了飯菜,也像那種方法。劉俶安排知遠,取西槽的馬,送大使到前邊的驛館,並讓道奴備好東槽的馬,親自送大使上路。一會兒馬到,敬立騎西槽的馬而行。劉俶也跟著走。走了二里地,劉俶就執手告別返回,和平常的館官不同。分別後走了幾里,敬立感覺所借的馬,有人糞的穢氣,一會兒漸漸味大,於是換自己的馬騎。走了四五里,東方像要亮了,前邊驛館正好有官吏迎拜。敬立吃驚的說:"我才出驛館呀。"說:"前館沒有人,大使憑什麼住宿?"大驚。到問所送的馬匹,全都不見了,那所馱的輜重,已退回百餘步放到路邊。到了前館,館吏說:"從前有原做鳳州河池縣尉的劉少府的殯宮,在那驛館的後園,早已廢毀。"敬立回去驗證它,廢館再無什麼東西,只是牆後有個古殯宮,東廠前有個搭鞍的木馬,西側中有個高腳木馬,門前有廢土堡兩座,殯宮前有殉葬品數人。敬立漸漸感覺嗓子眼有生食味,一會兒,吐出昨夜所吃的食物,都是腐爛味,像黃衣曲塵的顏色,這是棺材裡送給死人的食物,童僕等人都大吐,三日後才復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