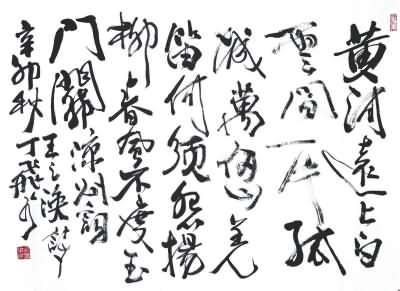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為駕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為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縶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即與僕輩陰於林下,糧餼什具,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於土官,去二日不見返。饑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洎童僕皆環火假寤。夜深忽寢。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睢盱,言語凶謾。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睹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沒,涸然古岸,俟為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瞷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眾,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為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為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日:「瑣事耳,為君召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為壇,仍列刀水,而膠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叫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為風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墠,暮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奸蠹,數以罪狀。升求衷俯狀,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凶尤甚,實為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斥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異聞集》)
【譯文】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年,在鄂渚遊覽,因為要去江陵,途中大受船夫王升的侮辱。宗仁剛剛舉為進士,沒有能力制服他,只好總是寬容他。到江陵後,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在任的官員,王升受到重重的鞭笞。宗仁用別的船上三峽,從荊州出發不到十天,所乘的就船失去了纜繩,篙桿和槳櫓都不能控制。船夫說:「這隻船已被仇人施了法術了,要不,昨天在水上哪能總出故障呢?現在無法往前走了,不到五百米處要經過石灘,其艱難險阻為一江之最。估計仇人的險惡用心在此,揣度我們的船到那裡時,必然觸礁船碎沉水。我們還是預先有所準備為好。」宗仁便跟僕人下船上岸,用一條大繩子索著船,沿岸順流而行。第二天到了石灘的地方,船隻果然顛簸衝撞,恣意升沉,很快就破碎了。因為有那條大繩子,人員幸無傷亡;但是船上的物品卻蕩然無存。峽岸上的道路幽深偏僻,上下數百里沒有人煙,宗仁只好與僕從們暫蔽於林蔭之下,吃的用的一無所有,險惡勞累,憂悶備至。派人報告當地官員,去了兩天仍未返回來。飢餓困頓,已臨絕境。那天夜裡,堆柴升火,宗仁與僮僕都圍著火堆和衣而睡。夜深時他猛然醒來,看見五個山裡的獵人坐在那裡,相貌特異,都拿著利器,瞪著眼睛張望,言語魯莽。假如他們揮刀上來,宗仁他們則只有束手等死而已。宗仁見他們要到跟前來,便高聲說道:「你們的家業該就在這山裡,我不幸船隻破碎,全部物品都沉沒了,困在岸上,等著豺狼來收拾我們。你們圓頭橫目,亦不為我們難受著急,而且公然笑侮,幸災樂禍以至如此。我現在斷糧已經一天多了,你們家住附近的可趕快回去做飯,拿來救救我們這些快死的人。」他們互相看了看,便叫二人起來回去做飯,不到天亮就帶著米肉鹽酪之類回來了。宗仁借這些東西維持生命,以等待回信。他向他們說明船撞碎的原由,山獠說:「在峽裡行此術的人很多,所以遭遇此難的也很多。但是,別人施行此術或者還能解除,唯獨王升施行此術時,非沉船不可。不知究竟是不是這小子干的。南山上有個叫白皎的人,法術通神,可以請他來,遣召行禁。我知道皎的住處,替你們請請看看。」宗仁誠懇地相求於他,那個山獠就去了。第二天,白皎果然來到,他頭戴黃冠身穿野服,手拄枴杖腳穿草鞋,一副山野之人的姿態相貌,禽獸是他的祖宗。宗仁又將這次歷險遭困的緣由跟他說了一遍。皎笑道:「小事一件。我替你把他召來殺了。」他清除草木,劃地為壇,擺上刀和水,自己站在中間。夜深月明,水碧山青,樹影朦朧,溪水潺潺,不斷聽到皎在引氣呼叫召唉王升的聲音,發聲清晰悠長,回音遼遠飄渺,遠達曙光到不了的地方。宗仁悄悄對僕使說:「難道七百里遠的王升,這一聲叫喚就能傳到他那裡嗎?」皎又詢問宗仁:「物沉船破,真如你說的那樣?莫不是因為風大浪急才出了事麼?」宗仁與船夫又把真實經過告訴了他。皎說:「果真如此,王升怎麼能跑沒影了呢?」又對宗仁的手下人說:「既然這樣,請把主人三代的名字告訴我,我才能推斷王升用的是什麼法術。」僕人便如實告訴了他。皎到山林深遠處另建了一個壇台,晚上再召呼王升,長呼的聲音跟昨天一樣。過了很長時間,山裡面忽然有人應答王皎,嗚咽之聲低微,藉著風才能聽到。很久。這個人便來王皎面前,原來是王升的魂魄。王皎斥責他奸凶狠毒,歷數他的罪狀。王升跪在地上叩頭求饒,臉都叩破了流出血來。王皎對宗仁說:「他已甘願服罪,可以把他殺死了。」宗仁說:「論他的奸詐凶殘之嚴重,實在難以寬恕,要是施行斬殺,則不可以,應該給他增加別的痛苦。」王皎便喝叱王升道:「保全你的軀體,要你身染血痢,百日而死。」王升哭泣著去了。王皎告辭,宗仁脫下自己的衣服贈送王皎,皎笑而不受。過了一會兒,船隻到了,宗仁乘船進發江陵。打聽王升的下落,王升就在被皎召去的那天在家裡染上了血痢,一百天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