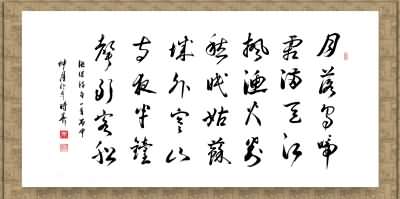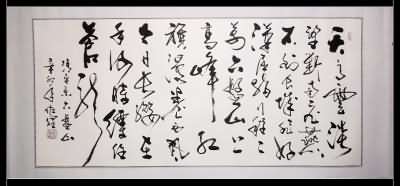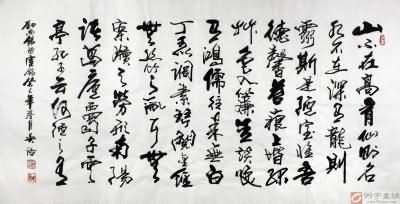作者或出處:蒲松齡
古文《胭脂》原文: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占卜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所以及笄未字。
對戶龐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首、趨去。去既遠,女猶凝眺。
王窺其意,戲謂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裡,故識之。近以妻服未闋,故衣素。娘子如有意,當寄語使委冰焉。」女無語,王笑而去。
數日無耗,女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就。邑邑徘徊,漸廢飲食;縈念頗苦,寢疾懾頓。
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漸覺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莫非為此?」女赬顏良久。王戲曰:「果為此,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其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可?」女歎氣曰:「事至此,已不能羞。若渠不嫌寒賤,即遣冰來,病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頷之而去。
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其有機可乘。欲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闥甚悉。
次夜,逾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女問:「誰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郎果愛妾,但當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玉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逮入,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鳴呼,品行虧損,兩所無益!」
宿恐假跡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癒。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
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王,不應。疑婦藏匿,婦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巳,遍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猶意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亦復杳然。
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下,踏一物,軟若絮綿,拾視,則巾裹女舄。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息而出。
逾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捨。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跡,知為女來。大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翁。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能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女,女哭而實告之;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
天明,訟於邑。官拘鄂。鄂為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處子,被執駭絕。上堂,不能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實,橫加梏械。生不堪痛楚,遂誣服。
及解郡,敲扑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質;及相見,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經數官復訊,無異。
後委濟南府複審。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其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盡得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問。生曰:「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側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關涉。」
公罷質,命拘王氏。拘到,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曰:「不知。」公詐之,曰:「胭脂供,殺卞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婦呼曰:「冤哉!滔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姦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雲無?」王曰:「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
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非良士!」嚴械之。宿供曰:「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曰:「逾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亦誣承。招成報上,咸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
然宿雖放縱無行,實亦國名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且又憐才恤士,宿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
問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有。」公曰:「淫婦豈得專私—人?」又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挑者。供云:「同裡毛大,屢挑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貞自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饋贈,曾一二次入小認家。」蓋甲、乙皆巷中遊蕩之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
既齊,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訊曰:「曩夢神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夾之;括發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使鬼神指之!」
使人以氈褥悉障殿窗,令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投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系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
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煙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
……(這裡刪去判決書全文。判決是:宿介,革去秀才,杖責釋放;毛大:死刑;胭脂及鄂秋隼,令縣令作媒,結為夫妻。)
案既結,遐邇傳誦焉。
自吳公鞫後,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賤,日登公堂,為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為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令為主委禽,送鼓吹焉。
《胭脂》現代文全文翻譯:
東昌府姓卞的牛醫,有個女兒,小名叫胭脂。胭脂又聰明又美麗。她父親很疼愛她,想把她許配給書香門第,但是那些名門望族卻嫌卞家出身低賤,不肯和他家結親。因此,胭脂已長大成人,還沒有許給人家。
卞家對門龐家,他的妻子王氏,性格輕浮愛開玩笑,是胭脂閨房裡閒聊的朋友。有一天,胭脂送王氏到門口,看見一個小伙子從門前走過,白衣白帽,很有丰采。胭脂見了,動了心,美麗的眼睛盯住了看他。小伙子低下頭,急急走了過去。他走遠了,胭脂還是望著他的背影。
王氏看出她的心思,開玩笑說:「像姑娘這樣的聰明美貌,如果配上這個人,那才稱心呢。」胭脂兩頰漲紅了,羞羞答答不說一句。王氏問:「你認識這個小伙子嗎?」胭脂說:「不認識。」王氏說:「他是南巷的秀才,叫鄂秋隼,父親是舉人,已經死了。我從前和他家是鄰居,所以認識他。現在身上穿著白衣服,因為他妻子死了還沒脫孝。姑娘如果有心,我去帶信,叫他找媒人來說親。」胭脂只不開口,王氏笑著走了。
過了好幾天,得不到王氏的音訊,胭脂疑心王氏沒有空閒到鄂秋隼那裡去,又疑心人家做官的後代不肯俯就,想來想去,悒悒不樂,思想裡丟不開那個人,非常苦惱,漸漸地不想吃東西,病倒在床,神情疲睏。
正好王氏來看望她,見她病成這樣,就追問她得病的根由。她回答說:「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從那天和你分別以後,就覺得悶悶不樂,生成了這病,現在是拖延時間,早晚保不住性命了。」王氏低聲說:「我的男人出門做買賣沒有回來,所以沒有人去帶信紿鄂秀才,你生病,不是為了這件事?」胭脂紅著臉,好久不開口。王氏開玩笑說:「如果真為這件事,你都病成這樣,還有什麼顧忌的?先叫他夜裡來一次聚一聚,難道他會不肯?」胭脂歎口氣說:「事情到這個地步,已經顧不上羞恥了。只要他不嫌我家低賤,馬上派媒人來,我的病自會好;如果偷偷約會,那萬萬不可以!」王氏點點頭,就走了。
王氏在年輕時就和鄰居的書生宿介有私情。出嫁以後,宿介一打聽到她男人出門到外地,就要來和她敘舊交情。這天夜裡,正好宿介來,王氏就把胭脂說的當作笑話講給他聽,還開玩笑地叫他轉告給鄂秋隼。宿介向來知道胭脂長得俊俏,聽見了心中暗喜,認為有機可乘。本想和王氏商量,又怕她吃醋。他就假當無心,用話打聽胭脂家裡房屋路徑,問得很清楚。
第二天夜裡,宿介翻牆進入卞家,直到胭脂臥室外面,用手指敲窗。胭脂問:「是誰?」宿介回答:「我是鄂秋隼。」胭脂說:「我想念你,為的是終身,不為一夜。你如果真心愛我,只應該早些請媒人來我家,如果說要私下裡不正經,我不敢同意。」宿介假裝答應,苦苦要求握一握她的手作為定約。胭脂不忍心拒絕他,勉強起床開房門。宿介急忙進門,就抱住了她要求親熱。胭脂沒有力氣抗拒,跌在地上,上氣不接下氣。宿介馬上拉她起來。胭脂說:「你是哪兒來的壞坯子,一定不是鄂秀才。如果是鄂秀才,他是溫柔文靜的人,知道了我生病的根由,一定會愛憐體恤我,哪會這樣粗暴的!你若是再這樣,我就要喊叫,結果壞了品行,我和你都沒有好處!」
宿介恐怕自己冒名頂替被識破,不敢再勉強,只是要求約定下次再會面的日期。她約定到結親那一天。宿介說,那太久了,再請她說個日子。她討厭他糾纏不清,就約定等她病好以後。宿介要她給個憑證,胭脂不肯。宿介就捉住她的腳,脫下她一隻繡花鞋出房門。胭脂叫他回來,對他說:「我已經把身體許給你了,還有什麼捨不得的。只是恐怕事情弄僵,給人講壞話。現在,繡花鞋已經到你手裡,料想你是不肯還我的。你將來如果變心,我只有一條死路!」
宿介從卞家出來,又到王氏那裡去過夜。睡下以後,心裡還想著那鞋子,暗地裡摸摸衣袖裡,鞋子竟不見了。馬上起來點燈,抖衣服搜尋。他問王氏拿沒拿他的東西,王氏不睬他,就疑心王氏把鞋藏了。王氏見他急成這樣,故意笑他讓他疑心,逗他講明白。宿介知道隱瞞不住,就把實情都說給她聽。講完,就打著燈籠在門外各處找,還是找不到。他心中懊惱,只得回房睡覺,私想幸而深夜沒有人看見,那只鞋掉了,一定還在路上。一清早起來出門去找,到底沒有找到。
先前,街坊上有個叫毛大的,游手好閒,沒有職業,曾經勾引過王氏,沒有得手。他知道宿介和王氏私通,總想捉住他們來脅迫王氏。這一天夜裡,毛大走過王氏門口,推推門,門沒有閂上,他就偷偷走進去。剛到窗外,腳下踏到一樣東西,軟綿綿的。抬起來一看,是汗巾包著的一隻女鞋。他伏在窗下偷聽,聽到宿介講拿到這鞋前後經過,聽得很清楚。他高興極了,就抽身出來。
過了幾夜,毛大夜裡爬牆進入到胭脂家。因為不熟悉門戶,錯撞到卞老漢屋裡。老漢向窗外張望,看見一個男人,看他那副樣子,知道是為他女兒而來的。老漢滿心忿怒,拿起把刀趕出來。毛大一見,大吃一驚,反身就逃。剛要爬上牆,卞老漢已經追到,毛大急得無處可逃,回過身來把老漢手裡的刀奪過來。胭脂的娘也起來了,高聲喊叫。毛大逃不脫,就用刀殺死了老漢,翻牆走了。胭脂的病已經好了一些,聽見鬧聲,才爬起床出來。娘和女兒一起打了燈籠一照,只見老漢頭腦開裂,已經說不出話來,一會兒就斷氣了。在牆腳根拾到一隻繡花鞋,一看,是胭脂的鞋。老太就逼問女兒說是怎麼回事,胭脂哭著把過去的事告訴了娘,但是不忍心連累王氏,只說是鄂秋隼自己上門來的。
天亮之後,告到縣裡。縣官派人拘捕鄂秋隼到案。鄂秋隼為人拘謹,不會講話,年紀十九歲了,看到生人又羞又怯像個大姑娘,被捕後嚇得了不得,上公堂,不知說什麼好,只會發抖。縣官看他這樣,格外相信他殺人是實,對他用重刑。這個書生受不了刑罰痛苦,就這樣屈打成招。
犯人解到府裡,審堂時又像縣裡一樣,嚴刑拷打。鄂秋隼冤氣沖天,每次—土堂,想要和胭脂當面對質,到碰面時,胭脂總是大罵,罵得他不敢說話,有口難分,這樣,就被判處死刑,官司一次次複審,經過了好幾個官員的手,大家認為判決沒有錯。
此後,這公案交給濟南府複審。當時,濟南太守是吳南岱。他一見鄂秋隼,不像個殺人兇犯,心裡疑惑。他就私下叫人慢慢地問他,讓他說出全部經過。聽到這些話以後,吳太守更相信這鄂秋隼是冤枉的。他考慮了好幾天,才開庭審問。先問胭脂:「那天夜裡你和鄂秋隼訂約以後,有人知道這件事嗎?」胭脂回答:「沒有人知道。」「開頭那天你看到鄂秋隼走過家門時,你旁邊有人嗎?」回答也是:「沒有人。」又叫鄂秋隼上堂,先用好話安慰他,叫他好好講。鄂秋隼說:「那天走過她家門口,只見我舊鄰居王氏和一個少女出來,我就急忙走開了,並沒有和她說一句話。」吳太守就呵斥胭脂:「剛才你說旁邊沒有人,怎麼出來個舊鄰居王氏呢?」立刻要對她用刑。胭脂害怕了,就說:「是有個王氏在旁,但是,事情和她無關。」
吳太守退堂,下命令拘捕王氏。幾天之後,王氏拘到。太守不讓王氏和胭脂見面說話,立刻升堂審問。他問王氏:「殺人兇手是誰?」王氏回答:「不知道。」太守騙她:「胭脂已經招供,說殺死卞老漢的事,你全部知道,你怎麼還不招!」那婦人大叫起來,「冤枉啊!那騷丫頭自己想男人,我雖然說了做媒的話,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她自己勾引姦夫進門,我怎麼知道!」太守再細細審問,王氏才講出前前後後開玩笑講過的話。太守又叫胭脂上堂,怒沖沖問:「你說王氏不知情,現在她怎麼自供說為你做媒啊?」胭脂哭著說:「自己不長進,讓老父慘死,官司結案不知要到哪,—年,去連累別人,心中不忍啊!」太守問王氏:「你對胭脂說了玩笑話之後,曾經告訴過誰?」王氏供:「沒對誰說過。」太守發怒說:「夫妻在床上,什麼話都會講,怎麼說沒有對人講過?」王氏供:「我男人出門在外,長久不在家了。」太守說:「凡是戲弄別人的,都笑別人愚笨,來誇耀自己聰明,你說沒對一個人講過,騙誰?」下令夾她十個指頭。王氏沒法,只得供出:「曾經和宿介講過。」於是太守下令釋放鄂秋隼,拘捕宿介。
宿介拘到,在審問中,他供:「殺人的事,不知情。」吳太守說:「和下流女人一起睡覺的決不會是好人!」用大刑拷問。宿介就供出:「騙胭脂,是事實,但是繡花鞋丟失以後,就不敢再去了。殺死人,實在不知情。」太守說:「翻牆頭的人,什麼事幹不出來!」再用刑。宿介熬不住刑,只得招供殺了人。口供上報,沒有人不稱讚吳太守精明能辦案。鐵案如山,宿介只等秋後伸頸處決了。
但是那宿介雖然行為放蕩,倒是個山東才子。他聽說學使施愚山的才能是人人稱頌的,又愛護有才能的人,他就寫了狀子,托人呈送給學使,說他是冤枉的。狀子上詞句沉痛悲慘。施學使把這案子的招供材料調來,反覆閱讀研究。他拍了桌子說:「這個書生真是冤枉的!」他就商請撫台、臬台,把這案子移給他再審。
他問宿介:「那繡花鞋掉在哪裡?」宿介供:「忘記了,但我敲王氏門的時候,還在袖子裡。」學使回頭問主氏:「除了宿介,你還有幾個姦夫?」王氏供說:「沒有。」學使說:「淫亂(版權所有https://FanYi.Cool古文翻譯庫)的婦人,哪會只姘一個?」王氏又供:「自己和宿介,年輕時就來往,所以不能拒絕他。以後不是沒有想勾引我的,但是我實在不敢順從他們。」要她指出勾引她的是哪幾個人,她說:「同街坊的毛大,曾經幾次來勾引,我幾次都拒絕他的。」學使說:「怎麼會忽然清白起來了?」叫人用鞭子打。那女人趴在地下只管磕頭,額上全是血,竭力分辯是沒有另外的姦夫,才不追問了。又問她:「你男人遠出外地,難道沒有借口什麼事到你處來的人?」王氏說:「那是有的,某甲、某乙,都因為要借錢給我,送東西給我,曾經來過一二次。」那某甲某乙都是街上的二流子,都是對這女人有意,還沒有做出什麼來的。學使把他們的名字也都記下,下令把這幾人全都拘捕,聽候審問。
人犯全部傳到之後,施學使帶了人犯到城隍廟,叫他們都跪伏在香案前面,對他們說:「前幾天我夢見城隍菩薩,他告訴我,殺人犯就在你們四五個人之中。現在你們面對城隍,不要說假話,如果能自首,可以寬大量刑;如果說假話,查出來就法不輕饒!」幾個人異口同聲,都說沒有殺過人。學使下令把刑具搬來放在地上,叫人把人犯頭髮紮起,衣服脫去,準備用刑。他們齊聲叫冤枉。學使就叫人把刑具撤去,對他們說:「既然你們不肯招認,那就要請菩薩來把兇手指出來!」
他叫人用毛氈被褥把大殿的窗戶全部遮住,不讓漏一點光線。把人犯的背都袒露著,趕到暗室裡,給他們一盆水,叫他們先洗洗手,分別用繩子拴在牆下,命令他們:「面對牆壁站好,不准動。殺人兇手,城隍菩薩會在他背上寫字的。」關了一會兒,把他們叫出來,查看每個人的背脊,指著毛大說:「這是殺人的兇手!」
原來施學使先叫人把灰塗在牆上,又叫人犯在煤灰水裡洗手,那兇手伯菩薩在他背上寫字,把背靠在牆上,所以背上沾上了灰色;臨出來,又用手掩住背脊,背上又沾上了煤煙色。學使本來疑心毛大是殺人犯,這樣就證實了。把他用了重刑,他就把殺人前後經過如實招供了。
……
定案之後,遠遠近近都把這無頭案傳開了。
自從吳太守審問之後,胭脂才知道鄂秋隼是冤枉的。每次過堂看到他,總是滿面羞慚,眼淚汪汪,好像有許多愛惜他的話而又說不出口。鄂秋隼很感激胭脂對他的癡情,對她也真心愛慕;但是想到她出身微賤,而且一次次上公堂,給千百人看到又指點,恐怕娶了她被人訕笑。日日夜夜盤算,不知怎麼才好。等到判詞下來,知道官家作媒與她結合,這才定下心來。後來縣令就出面為他定親,派了吹鼓手,給他兩個辦了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