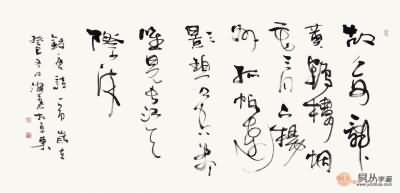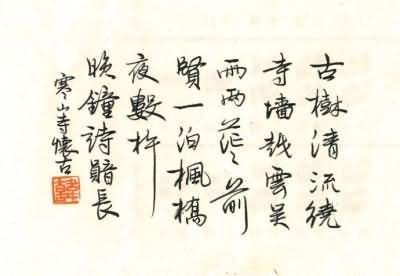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
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有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
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
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禮開始製作的時候,雖然很難但很容易施行,等到施行了以後,雖然容易卻又難以持久。
天下人都還不知道君王有君王的威嚴,父親有父親的威嚴,兄長有兄長的威嚴,而聖人讓君王父兄之名得以彰顯。 天下人不知道君王父兄之間的區別,而聖人讓他們懂得了拜起站立之禮。天下人不肯聽從聖人之說而行拜起站立之 禮,是聖人以身作則,讓他們有了羞恥之心而依照聖人的教導而行。哎呀,這是很困難的呀。天下人厭惡死亡已經 很久了,聖人招來他們對他們說:過來,我讓你們得以生存。然後他的方法果真可以讓天下人得以生存,天下人看 到他們之前所處的境地是如此危險,而現在所處的境地是如此的安全,將會何去何從呢?因此那個時候,雖然製作 很難卻很容易施行。等到施行以後,天下人對待他們的君王父兄,就像看頭和腳一樣不需要加以辨別就知道了,對 於拜起站立之禮就像是睡覺吃飯一樣不需要告訴他們就自然去做。雖然這樣,一百個人都能夠服從,如果有一個人 不服從,他的處境也不至於馬上就陷於死地。而天下的人,不知道最初的時候沒有禮就會陷於死地,卻看到了如今 雖然沒有禮卻還不至於陷於死地,便說道:聖人欺騙了我。因此在那個時候,禮雖然容易施行卻很難持久。哎呀, 聖人所持有的用來戰勝天下人勞逸的,只有死生這個說法而已。一旦死生之說不被天下人所信任,那麼勞逸之說就 會冒出來並且獲勝。一旦勞逸之說獲勝,那麼聖人的權勢也就失去了。 酒中出現了鴆毒,肉中出現了堇毒,然後人就不再敢喝酒吃肉了。藥可以讓快要死去的人活過來,然後人就不 再逃避藥的苦口了。一旦去掉鴆毒,清除了堇毒,那麼酒肉的效力就能夠勝過藥。聖人開始製作禮的時候,他也知 道以後的形勢也將必定如此,說道:告訴別人事實和真相,然後別人才能夠相信。幸運的是,如今我用來告訴人民 的,其道理是一樣的,並且事實也如此,因此人們才相信。我知道其中的道理,天下人知道相應的事,如果事情有 虛假的,那麼我的道理就不足以讓天下人為之信服了,這就是告訴給他們的話有做不到的地方。如果告訴他們的話 有做不到的地方,那麼必定有人會悄悄地驅逐並且潛隱地率領。於是通觀天地之間,我認為能夠得到最神明的機運, 竊取它來作為樂。 我看到雨是用來讓萬物潤濕的,太陽是用來讓萬物乾燥的,風是用來讓萬物流動的,發出隱隱的聲響的是雷霆, 它有什麼作用呢?陰雲凝聚在一起而不消散,萬物蹙迫在一起而不舒展,雨不能將其潤濕、太陽不能將其乾燥、風 不能將其吹動的那些東西,雷霆一震就能讓那些凝聚的東西散開,侷促在一起的東西舒展開。名字為雨的,名字為 太陽的,名字為風的,所起作用的都是形,而名字為雷的,所起作用的則是神。而有用的莫過於聲音,所以聖人便 憑借聲音獲得樂。
區別君臣、父子、兄弟之別的,是禮,而禮所不能起作用的地方,樂則能起作用。醇正的聲音進 入了人的耳朵,人就都會興起侍奉君王、侍奉父親、侍奉兄長之心,那麼禮是我心中原本就有的,這樣一來對待聖 人的言說,又怎麼會不相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