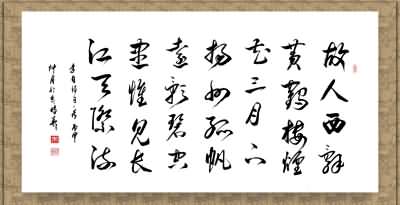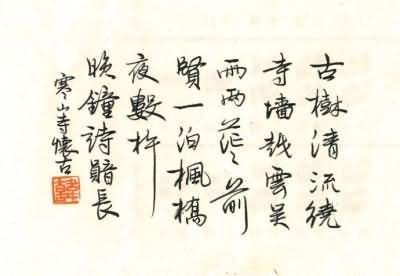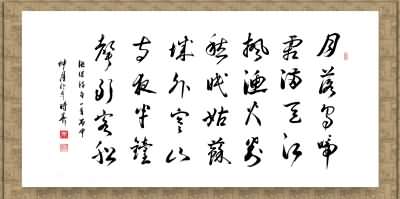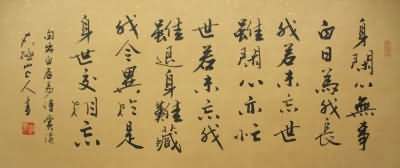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奸。」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於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為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即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於弁詣質,質怒前不為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籠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揚,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卻回,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頻有章奏諫。曰(明抄本無曰字)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即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眾,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流崖州,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即賈直言之父也。(出《異聞集》)
【譯文】
穆質初應舉,考試結束,與楊憑等數人相會。穆在策論中說:「防賢甚於防奸。」楊憑說:「你說得不對,當今天子正在禮待賢士,怎麼說防賢甚於防奸呢。」穆說:「果然這樣那就對了。」他們便出去謁見鮮於弁,鮮於弁待穆甚厚。飯還沒吃完,僕人報告說:「尊師來了。」弁急忙跑去穿上朝靴帶好笏板,然後命人撤掉飯菜。來人進屋後,原來是一個瞎老道而已。穆很惱火鮮於弁待他禮薄,而且來的又是個瞎道士,所以不向來人行禮,依然安坐不動。過了一會兒,道士對穆說:「您難道不是吃奉祿的官人嗎?」答道:「不是。」又問他曾經上封事進書策而求官祿沒有,穆說:「現正在應制,已經通過考試。」道士說:「你的臉色上有大喜。及第的同時,還要在天子身邊為官。本月十五日午後,你就知道了,策論是第三等,官位是左補缺,所以我先告訴你。」穆質告辭走了。到了十五日,剛過午,聽見敲門聲很響很急,打發人前去應對,報說:「五郎官拜左補缺。」當時,不先唱報「第三等」就是同時任了官職,要一塊兒拜接喜報,所以才有剛才那樣的報法。後來鮮於弁來見穆質,穆生氣那天沒讓他吃完飯,不與他見面。弁又來,質見了他,弁說:「前幾天那個道士就是賈籠,他料事如神,我們應該去拜見他。」質便與弁一塊兒去拜見。賈籠對穆質說:「後三月至九月,不要吃羊肉,你能得坐兵部員外郎職位,又有知制誥的官銜。」德宗皇帝曾經賞識穆質,說:「每愛卿對策,所說的事情多有可行的。」穆質已存在更大的希望,內心很看輕知制誥,私下裡對人說:「一個人該做什麼官天生就有這個運氣,哪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誥的道理。這純粹是道士的妖言呀!」於是他又像過去一樣吃起羊肉來。到了四月,給事趙憬忽然召見穆質說:「咱倆共同去找一個異人。」到那裡一看,就是以前見過的那個瞎子道士。趙憬像弟子一樣致敬行禮,致謝之後方才落座。道士對穆質說:「以前不讓你吃羊肉,到九月能得制誥。為什麼不講信用?如今不同了,莫不是還有災禍嗎?對了,你有厄運!」穆質說:「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吧?」道士說:「本來很危險,因為你認識皇上,才能免除一死呵!」穆質問道:「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答:「如今無計可施了。」質又問:「若遭貶遷,多長時間能夠回來?」道士說:「最少是十五年。補缺要回去,貧道不能看見。」於是與他握手告別,不再說什麼。沒過多久,宰相李泌奏稱:穆質和盧景亮在大會中,都說自己不斷有章奏進諫,國家有善政,他們就說是自己出的主意;有壞事就說是他們苦諫皇上不採納;這種做法定以迷惑眾人,應當以大不敬論處,請交給京兆府裁決斬殺。德宗說:「盧景亮我不瞭解,穆質我曾經相識,不要這樣對待他。」又進言打杖六十,流放崖州。皇上御筆親書命令給他一個官銜。於是把穆質往邊遠地方貶遷了。後來,到了十五年,憲宗皇帝才把他徵召入宮。賈籠就是賈直言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