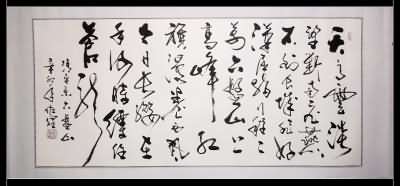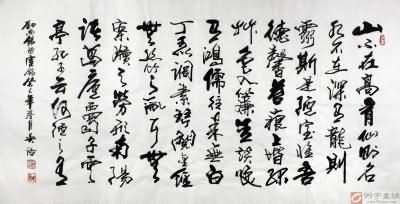《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蹶而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
兆符從余游,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闃qu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
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日:『 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為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饋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余為書抵饋金者。及報【報告,答覆】詔【告訴】,而死已彌月矣。
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寧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矻矻【k勤勉不懈的樣子】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瘀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
余與崑繩交最先,既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游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游。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
兆符性孤特,雖其父故交既宦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即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為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父節概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為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
雍正元年冬十二月,我生病無法起床。聽到王兆符先生暈倒後又甦醒過來,我趕緊乘轎去看望他,與他交流,他的精神氣息好像沒有變化,三天後就去世了。唉,他是我朋友王崑繩的兒子。
王兆符與我交往,是在丙子年的春天。我在京城時,我在姓汪的人家開學館,王崑繩住在王家,讓王兆符來向我求教,住在汪家的馬隊旁,端正地坐著默默地記誦,寂靜得像沒人一樣。正是盛夏時節,每天三次往返,不接受汪家一勺的湯水。
後來王崑繩離家隨意遊玩,王兆符從天津遷居到金壇,又在南京跟從我學習。王崑繩曾經對我說:「兆符對待你就像對待父親。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你和李剛主,我讓他跟隨李剛主學習,他說:『 我對於方先生的學問,還未能學完呢。』」王兆符成人後成了縣學的生員,遷居到南方後就離我而去了。過了四十歲,因為謀生來到京城。有人勸他參加鄉試,庚子年考中了京城地區的舉人,第二年考中了進士。有人贈送他錢物,讓他趕快做官來奉養母親。我說:「用這錢買田來耕種,那麼母親就可以奉養,學問可以增長,前人的學術著作可以窮盡了。」兆符憂愁不悅,催促我寫文章給贈送的錢物的人(說明情況)。等到有了回復,而他已經去世滿一個月了。
在兆符剛剛南遷時,憑著少年之身,獨自一人,帶著母親及姐姐妹妹跋山涉水三千里。等到王崑繩去世後,四方奔波,未曾有十天半月的安居。而他的母親年老多病,時不時地生氣。常常擔心妻子兒女身邊奴婢,時間長了無法忍受,因而在照看母親時不能竭盡誠心,所以身在他鄉,總是擔心家裡。又擔心年歲一天天增長,學問沒有長進,卻在繁雜的人事中勤勉不懈。因此心力耗盡,身形精神鬱積成病,一旦發作就不可救治了。
我和崑繩結交最早,不久又結識了剛主,三個人所學習的內容不同,但是志趣相投,三人的交情猶如一家人。剛主的長子習仁,也與我交往。辛丑年秋,剛主讓習仁到江南選擇地方居住,卻在路上去世。自從習仁去世之後,三人的後輩中,稟性德行沒有可以期望的了。現在又加上兆符去世,那麼在文學義理方面,可以與之深入交流的對象也很少了。
兆符的性格孤傲獨特,即使是他的父親的老朋友已經官位顯達,如果看到他們的神色與以往稍有不同,就不肯再見到他們了。他立身處世端方正直,並且憑借文學才能聞名於世,所以他生了病,聽說的人都為他擔憂,他去世後,眾人都對他感到可惜。兆符希望葬在先人的墓地,可是母親和妻子兒女卻生活在江南。葬禮結束,回到南方的讀書人中朋友,為他經營家庭,留在京城的朋友,分配好年份主辦墓地的祭掃。雖然是被兆符的志向氣概感召,但是他的祖父長久留在人們心中的操守氣概和聲望(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以被泯滅。王兆符享年四十五歲,所編撰的《周官》以及若干卷詩文,蔣湘帆先生為他編錄好並收藏起來。來等待他的兒子長大後交給他。
(節選自《望溪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