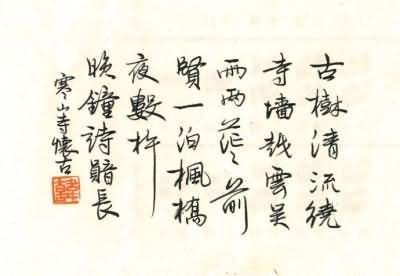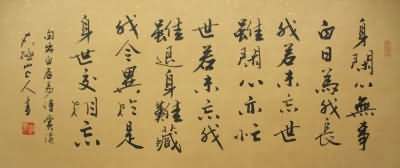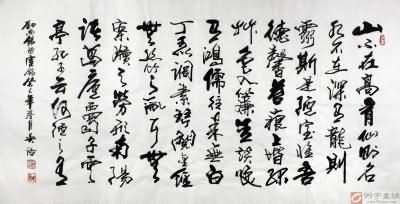《答尹似村書》
書來,怪僕悖宋儒解《論語》,僕頗不謂然。
孔子之道大而博,當時不違如愚者,顏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終有得失。趨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軻,博雅如馬、鄭,俱有得失。豈有千載後奉一宋儒,而遽謂孔子之道儘是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苟其得,雖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雖顏回,瞻之而在後。宋儒雖賢,終在顏、曾之下;僕雖不肖,或較童子有餘,安見宋儒儘是,而僕盡非也?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宋儒而果賢也,有不審問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一聞異己者而即怒,烏乎賢?必欲抹殺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亦如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有往往始願不及此,而後人報之已過者。關忠武忠於漢室,此其志也,豈料後之隆以帝稱哉?宋儒闡宣周、孔,此其志也,豈料後之垂為法令哉?且安知其著書時,不望後世賢人君子為之補過拾遺,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聖人之道乎?
自時文興,制科立,《大全》頒,遵之者貴,悖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止。此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習常隸舊,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冒不韙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法令也。法令與宋儒,則亦有分矣。
僕幼時墨守宋學,聞講義略有異,輒掩耳而走。及長,讀書漸多,入理漸深,方悔為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抱宋儒作狹見之迂士,並毋若僕聞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取材於《小倉山房詩文集》,有刪改)
【
您寫信來,責怪我違背宋儒的認識解釋《論語》,我實在不這麼認為。
孔子所講說的道理博大精深,當時像愚笨之人一樣對它不加違背的,就只有顏回了。有若、宰我他們的智慧足以瞭解聖人,最終有得有失。子思直接受到孔子的教導,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後來的馬融、鄭玄(漢代為《論語》做過注的學者)稱得上博雅,都有得有失。哪有數千年後只尊奉宋儒一派,而斷然說孔子的道理在他們那兒就都對了呢?《易經》說:「仁者見到它稱之為仁,智者見到它稱之為智。」孟子說:「道理像大路一樣,哪裡會難以理解!」如果有所得,即使是滄浪的童子,也能吟唱而心與之相通;如果無所得,即使是顏回這樣的亞聖,也會覺得高深難解。宋儒雖然賢明,終究不能超過顏回、曾參;我雖然不才,或許比滄浪的童子要聰明一些。怎麼知道宋儒都是對的,我都是錯的呢?
《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要廣博地學習,要詳細地追問求教)」《尚書》說:「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指勤於別人請教,學識就會淵博;只憑自己的主觀意圖行事,就辦不成大事)」假如宋儒果真賢明,會是不審問之人嗎?會是只管自己的狹小之人嗎?如果一聽到不同的意見就立刻發怒,哪裡稱得上賢明呢?如果一定要抹殺一切(解釋《論語》的學說),只是以宋儒為依歸,這也就和市儈等卑賤之人想要把持市場一樣了。古代人常常有開始並沒有料到(惟宋儒是歸這種情形),後人反應太過了的情形。關羽效忠於漢室,這是他的志向,哪裡料到後人尊崇他為帝呢?宋儒闡發宣揚周公、孔子的道理,這是他們的志向,哪裡料到後人尊崇其學說為法令呢?況且怎麼知道他們著書時不希望後世的賢人君子為他們補過拾遺,去除不對的,保存正確的,借此來合乎聖人的道理呢?
自從(科舉的)時文興盛,以宋儒之說應對科舉的制度確立、《性理大全》頒布以來,遵循宋儒學說的就能獲得貴勢,違背它的就只能處於卑賤的地位,這樣之後就束縛住了天下之人的聰耳明目,要使他們像僧人照著經文誦經、伶人照著樂譜歌唱一樣才罷手。這不是宋儒的過錯,是尊奉宋儒之人的過錯。現在天下有兩個弊病,平庸之人多習慣附屬與平常的舊習,就是這樣都忙不過來,哪裡能夠另外有新的發現?那些才能優秀之人,又多浮泛粗淺地讀書,不願意冒著錯誤被指責的風險去深入研究。這兩種情形,都不是在尊奉宋儒,而是在尊奉朝廷的法律命令。法律命令與宋儒,也是有區分的。
我自幼墨守宋學,聽到講義中有不同的觀點,總是掩耳而走。長大後,讀書漸多,對道理的理解逐漸加深,才後悔被古人所束縛。您也應早早醒悟,不要固執宋儒的學說,成為(孤陋寡聞的)迂腐之人,並且不要像我這樣因為聞道太晚,以致於找不到瞭解這個道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