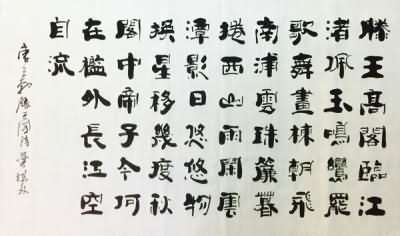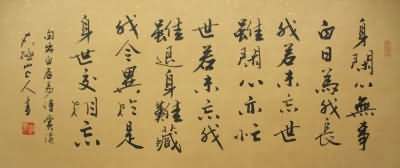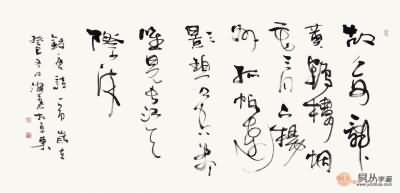原文
俞慎,字謹庵,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捨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捨光潔;然門庭踧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以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媼。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為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捨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復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搴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媼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
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誤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碗流炙。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婚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捨捨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猶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慼慼於得失,故不為也。」
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寧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逾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噪,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卻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尚強作噱;恂九失色,酒琖傾墮,身僕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菉。銜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矣!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沒後,急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
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冠巾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異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佈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恂九不欲。既沒,公子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
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吊,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所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裡。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鹹讚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系念之,每月輒一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還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庵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慮韓詐諼,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啟簾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逴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眾竊喜其可以問途。
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眾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取婢歸,細詰情跡,微窺其變,忿甚,遍愬都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能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及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枝;家人搒掠殆遍,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瘐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綦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
逾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媼,驀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笑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欲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家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婚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床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婿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逾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
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幛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髭發盡黑,猝不能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裡,曰:「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遍訪之,竟無蹤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如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聊齋之素秋白話翻譯:
俞慎,字謹庵,出身於順天一個官宦世家。他進京趕考時,住在郊區一所房子裡,經常看見對門有一個少年,生得美如冠玉,心中很喜歡他。使漸漸接近他,同他交談。少年談吐尤其風雅,俞慎更加喜愛,拉著他的胳膊來到自己的住處,設酒宴款待。問他的姓氏,少年自稱是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俞慎聽到與自己同姓,更覺親近,就同他結拜為兄弟。少年便將自己的名字減去「士」字,改為俞忱。
第二天,俞慎來到俞恂九家,見書房、住處明亮整潔,但門庭冷落,也沒有僕人、書僮。俞恂九領著俞慎進入室內,招呼妹妹出來拜見,他妹妹年約十三四歲,肌膚晶瑩明澈,就是粉玉也不如她白。一會兒,俞恂九的妹妹又端來茶敬客,好像家裡也沒有丫鬟、女傭。俞慎感到奇怪,說了幾句話出來了。從此他們二人就像親兄弟一樣友愛。俞恂九沒有一天不來俞慎的住所,有時留他住下,他就以妹妹弱小無伴而推辭。俞慎說:「弟弟離家千里,也沒有個應門的書僮;兄妹倆又纖弱,怎麼生活啊!我想,你們不如跟我去,一同住在我那兒,怎樣?」俞恂九很高興,約定考完試後隨他回去。
考試完畢,俞恂九把俞慎請到家,說:「今天是中秋佳節,月明如晝。妹妹素秋準備了酒菜,希望不要辜負了她的一番心意。」說完,拉著俞慎的手來到內室。素秋出來,說了幾句客套話,就又進屋,放下簾子準備飯菜。不多時,素秋親手端出菜餚來。俞慎站起來說:「妹妹來回奔波,讓我怎麼過意得去。」素秋笑著進去了。一會兒,就有一個穿青衣的丫鬟捧著酒壺,還有一個老媽媽端著一盤燒好的魚出來。俞慎驚訝地說:「她們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不早點出來侍候,卻麻煩妹妹呢?」俞恂九微笑著說:「素秋又作怪了。」只聽到簾內吃吃的笑聲傳來,俞慎不解其中的緣故。到了散席的時侯,老媽媽同丫鬟出來收抬碗筷。俞慎正在咳嗽,不小心將唾沫吐到丫鬟衣服上,丫鬟應聲摔倒,碗筷菜湯撒了一地。再看那丫鬟,原來是個用布剪的小人,只有四寸大小。俞恂九大笑起來,素秋也笑著出來,撿起布人走了。不一會兒,丫鬟又出來,像剛才一樣奔忙。俞慎更加驚異,俞恂九說:「這不過是妹妹小時候學的一點小魔術罷了。」俞慎於是又問:「弟弟妹妹都已長大成人,為什麼還沒成親呢?」回答說:「父母已經去世,我們是留是走還沒有拿定主意,所以拖了下來。」接著兩人商定了動身的日子,俞恂九將房子賣了,帶著妹妹同俞慎一塊西去。
回到家後,俞慎教人打掃出一所房子,讓俞恂九兄妹住下,又派了個丫鬟侍候他們。俞慎的妻子,是韓侍郎的侄女,非常愛憐素秋,每頓飯都在一塊吃。俞慎同俞恂九也是這樣。俞恂九非常聰明,讀書時一目十行,試著作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些名望的老儒也比不上他。俞慎勸他去考秀才,俞恂九說:「我暫時讀點書,不過是想替你分擔些辛苦罷了。我自知福分淺薄,不能做官;況且一旦走上這條路,就不能不時時擔憂,患得患失,所以不想去考試。」
生了三年,俞慎考試又落了榜。俞恂九為他抱不平,奮然說:「榜上掛個名字,怎麼就艱難到這種地步!我當初為成敗所迷惑,所以寧願清清靜靜地生活。如今看到大哥不能施展文才,不覺心熱。我這十九歲的老童生,也要像馬駒一樣去奔馳一番了。」俞慎聽了很高興,到了考試的日期,送他去考場,結果他縣、郡、道三場都考了第一名。從此俞恂九與俞慎一塊更加刻苦攻讀。過了一年參加科試,兩人並列為郡、縣冠軍。俞恂九從此名聲大噪,遠近的人都爭著來提親,俞恂九都拒絕了。俞慎竭力勸說他,他就推說等參加鄉試以後再說。不久,鄉試完畢,傾慕俞恂九的人都爭著抄錄他的文章,互相傳誦。俞恂九自己也覺得必定名列榜首了。等到放榜,兄弟兩人卻都榜上無名。當時他們正在對坐飲酒,聽到這消息,俞慎還能強作笑語;俞恂九卻大驚失色,酒杯掉在地上,一頭撲倒在桌子下面。俞慎急忙把他扶到床上,恂九的病情卻已經十分危險了。急忙喊妹妹來,俞恂九睜開眼對俞慎說:「我們倆交情雖如同胞,其實不是同族。小弟自己感到快要死了,受你的恩惠無法報答。素秋已長大成人,既蒙嫂嫂撫愛,你就納她為妾吧。」俞慎生氣地說:「兄弟這是胡說什麼呀!你以為我是那種衣冠禽獸嗎?」俞恂九感動地流下眼淚。俞慎用重金為他購置了上等棺材,俞恂九讓人把棺材抬到跟前,竭力支撐著爬進去,囑咐妹妹說:「我死以後,立即蓋好棺蓋,不要讓任何人打開看。」俞慎還有話想說,俞恂九已經閉上眼睛死了。俞慎十分哀傷,如同死了親兄弟。可是私下裡卻懷疑俞恂九的遺囑奇怪。趁素秋外出,他偷偷打開棺材一看,見裡面的袍服像蟬蛇褪下的皮。揭開衣服,有一條一尺多長的蠹魚,僵臥在裡面。俞慎正在驚訝,素秋急匆匆地進來了,慘痛地說:「你們兄弟之間有什麼隔閡?我們所以這樣做,並不是避諱兄長;只是怕傳播聲揚出去,我也不能在這裡久住了!」俞慎說:「禮法因人情而判定,只要感情真摯,不是同類又有什麼區別呢?妹妹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嗎?就是你嫂嫂我也不會洩漏一句的,請你不要憂慮。」於是很快選定了下葬的日期,把俞恂九厚葬了。
當初,俞慎想把素秋嫁給官宦世家,俞恂九不同意。俞恂九死後,俞慎又同素秋商量這事,素秋不肯。俞慎說:「妹妹已經二十歲了,再不嫁人,人家會說我什麼呢?」素秋回答說:「如果是這樣,我就聽兄長的。但是我自覺得沒福分,不願嫁給富貴人家。要嫁,就嫁給一個窮書生吧。」俞慎說:「可以。」不幾天,媒人一個接一個的來,但素秋都不中意。先前,俞慎的妻弟韓荃來弔喪,見到過素秋,心裡非常喜愛她,想買她作妾,同他姐姐商量。姐姐急忙告誡他不要再說了,怕俞慎知道生氣。韓荃回家後,始終不死心,又托媒人傳信給俞慎,許諾為姐夫買通關節,保證他鄉試得中。俞慎聽了後,勃然大怒,將捎信的臭罵了一頓,打出門去。從此與韓荃斷絕了交往。後來又有個已故尚書的孫子某甲,將要娶親時,沒過門的媳婦忽然死了,也派媒人來俞慎家提親。某甲家宅第高大,家財萬貫,俞慎平素就知道,但想親眼見一見某甲本人,就同媒人約定日期,讓某甲親自來見。到了那天,俞慎讓素秋隔著簾子,在裡邊自己相看。某甲來了,身穿皮袍騎著駿馬,帶領一大幫隨從,向街坊四鄰炫耀自己的富有。再看他人長得秀雅漂亮,像個姑娘,俞慎非常喜歡。看見的人也都紛紛稱讚,但素秋卻很不樂意。俞慎沒聽索秋的,竟許了這門親事,給素秋準備了豐厚的嫁妝,花錢毫不計較。素秋再三制止,說是只帶一個大丫頭侍候就行了,俞慎也不聽,終究還是陪送得很豐厚。
素秋出嫁以後,夫妻感情很好,但是兄嫂常掛念她,每月總要回來一趟。來時,妝盒中的首飾,總要拿回幾件,交給嫂子收存。嫂嫂不知她的意思,姑且依從她。某甲從小父親就沒了,守寡的母親對他過分溺愛。他經常和壞人接觸,漸漸被引誘去嫖妓、賭博,家傳書畫、珍貴的古玩,都讓他賣掉還債了。韓荃與他相識,便請他喝酒,暗中試探他,說願用兩個小妾加上五百兩銀子交換素秋。某甲開始不同意,韓荃再三請求,某甲的心有些動了,但又怕俞慎知道不答應。韓荃說:「我與他是至親,況且素秋又不是他家中的人,如果事情辦成了,他也拿我沒辦法。萬一有什麼事,由我出面承擔。有我父親在,一個俞慎有什麼可怕的!」接著讓兩個侍妾打扮得漂漂亮亮出來勸酒,並且說:「如按我說的辦,這兩個女子就是你家的人了。」某甲被韓荃迷惑住了,約定好交換日期,就回去了。到了那天,某甲怕韓荃欺詐他,半夜就在路上等著,看到果然有輛車子前來。掀開簾子,見裡面的人果然不假,就領她們回家,暫且安置在書房裡。韓荃的僕人又拿出五百兩銀子,當面交清。某甲便跑入內室,騙素秋說,俞慎得了急病,叫她趕快回家。素秋來不及梳妝,急匆匆地出來,上車就走了。夜裡看不清方向,車子迷了路,走了很遠,也沒有到韓荃家。忽然看見兩支巨大的蠟燭迎面而來,大家暗暗高興,以為可以問路了。不一會,走到跟前,原來是一條巨蟒,瞪著兩隻像燈一樣的大眼睛。眾人害怕極了,人和馬都逃竄了,把車子丟在路旁。天明了才會齊回去一看,只剩下一輛空車子了。他們認為素秋一定是被大蟒吃了,回去告訴主人,韓荃只有垂頭喪氣而已。
幾天後,俞慎派人來看望妹妹,才知道素秋被壞人騙走了。當時也沒有懷疑是素秋的女婿搞鬼。直到陪嫁的丫頭回來,細說了事情的經過,俞慎才覺出其中有變故,不禁氣憤至極,跑遍了縣府到處告狀。某甲很害怕,向韓荃求救。韓荃因為人財兩空,正在懊喪,拒絕了他的要求,不肯幫忙。某甲傻了眼,沒有一點辦法。府、縣拘票來到。他只好賄賂衙役,才暫時沒被帶走。過了一個多月,金銀珠寶連同服飾全被他典賣一空。俞慎在省衙追究得很急,縣官也接到上司嚴加追查的命令。某甲知道再也不能躲藏了,才出來到公堂說出全部實情。省衙又下傳票,拘捕韓荃對質。韓荃害怕,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父親。他父親當時已退職在家,惱怒兒子的作為不守法,把他綁起來交給了衙役。韓荃到了各官府,說到遇見大蟒的變故,官府以為他是胡編亂造,將他的僕人嚴刑拷打,某甲也挨了好幾次板子。幸虧他母親整日變賣田產,上下賄賂營救,韓荃才受刑不重,免於一死,韓荃的僕人卻已經病死在獄中。韓荃長期囚禁牢中,願意幫助某甲送一千兩銀子給俞慎,哀救撤銷這樁案子,俞慎不答應。某甲的母親又請求再加上兩個侍妾,只求暫作疑案擱一擱,等他們去尋訪素秋。俞慎的妻子又受了叔母的囑托,天天勸解,俞慎才應允不再去催。某甲家中已經很貧窮,想賣掉宅子湊點銀兩,宅子一時又賣不出去,就先送了侍妾來,乞求俞慎暫緩交銀日期。
過了幾天,俞慎夜裡正坐在書房中,素秋同一個老媽媽忽然進來了。俞慎驚奇地問:「妹妹原來平安無事啊?」素秋笑著說:「那條大蟒是妹妹施的小法術。那天夜裡我逃到一個秀才家裡,和他母親住在一起。他說認識哥哥,現在門外,請他進來吧。」俞慎急得倒穿鞋子迎出去,拿燈一照,不是別人,原來是周生,是宛平縣的名士,兩人一向意氣相投。俞慎拉著周生的手進了書房,擺酒宴招待,親熱地談了很久,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來,素秋天將明時,去敲周生的門,周母接她進去,仔細詢問,知道是俞公子的妹妹,就要派人通知俞慎,素秋制止了,就和周母住在一起。周母看她聰慧,善解人意,很喜歡她。因為周生還沒有娶親,就想把她娶來給兒子作媳婦,還含蓄地透露了這個意思。素秋以沒有得到哥哥的同意而推辭。周生也因為與俞公子交情很好,不肯沒有媒人就成親。只是經常打聽消息,得知官司已經說情調解,素秋便告訴周母想回家。周母讓周生帶一老媽媽送她,並囑咐老媽媽作媒提親。
俞慎因為素秋在周家住了很長時間,也有意把素秋嫁給周生。聽說老媽媽是來作媒的,非常喜歡,就同周生當面訂好了這門親事。原先,素秋夜裡回來,是想讓俞慎得了銀子後再告訴別人,俞慎不肯這麼辦,說:「以前是因為氣憤無處發洩,所以想借索取錢財讓他們嘗嘗敗家的苦頭。如今又見到妹妹,一萬兩銀子也換不來啊!」馬上派人告訴那兩家,官司算了結了。又想到周生家不太富裕,路途遙遠,迎親很艱難,就讓周生母子搬來,住在俞恂九原來住過的房子裡。周生也備了彩禮,請了鼓樂隊,舉行了婚禮。
一天,嫂嫂同素秋開玩笑:「你如今有了新女婿,從前和某甲的枕席之愛還記得嗎?」素秋笑著問丫頭說:「還記得嗎?」嫂嫂感到疑惑,就追問她。原來素秋在某甲家三年,枕席之事都是讓丫頭代替的。每到晚上,素秋用筆給大丫頭畫好雙眉,讓她過去陪某甲。即便是對著蠟燭坐著,某甲也分辨不出來。嫂嫂更加驚奇,請求素秋教給她法術,索秋只笑不說話。
第二年,是三年一次的大會考。周生準備同俞慎一塊去趕考,素秋說:「不必去。」俞慎強拉著周生去了,結果俞慎考中了,周生落了榜。回來後便打算不再去應考了。過了年,周母去世,周生再也不提趕考應試的事了。
一天,素秋告訴嫂嫂說:「以前你問我法術,我本不肯用這些來惹別人驚駭。現在要離別遠去,讓我秘密傳授給你,也可以躲避兵火。」嫂嫂吃驚地問她緣故,素秋回答說:「三年後,這裡就沒有人煙了。我身體弱,受不住驚嚇,要去海濱隱居。大哥是富貴中的人,不能一起去,所以說要離別了!」就將法術全部教給嫂嫂。幾天後,素秋又告訴俞慎。俞慎留不住她,難過得流淚,問:「到什麼地方去?」素秋也不說。雞一叫就早早起來,帶一個白鬍鬚的老僕,騎著兩頭驢走了。俞慎叫人暗暗跟在後邊送她,到了膠州、萊州一帶,塵霧遮天,晴天後已經不知道她們往哪裡去了。
三年後,李自成率眾造反,村裡的房屋變成了一片廢墟。韓夫人剪個布人放在大門裡面,義兵來了,看到院子裡雲霧圍繞著一丈多高的天神守著,就嚇跑了。因此,全家得以安然無恙。
後來,村中有一個商人到海上,遇見一個老頭,像是素秋的老僕。但是老頭的鬍子頭髮全是黑的,不敢貿然相認。老頭停下笑著說;「我家公子還安康吧?請你捎個口信,素秋姑娘也很安樂。」商人問他住在什麼地方,老頭說:「很遠,很遠,」就急忙走了。俞慎聽說後,派人到海邊四處尋訪,竟沒有一點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