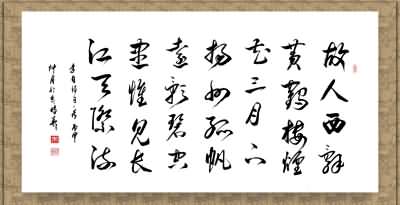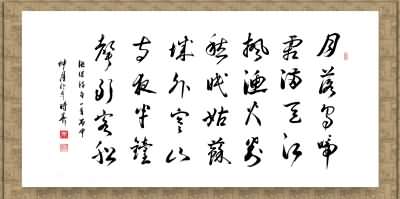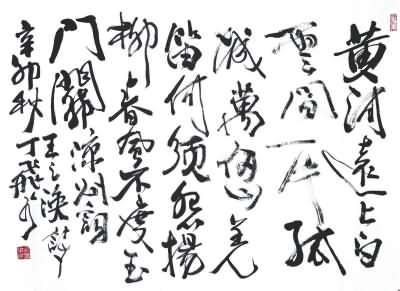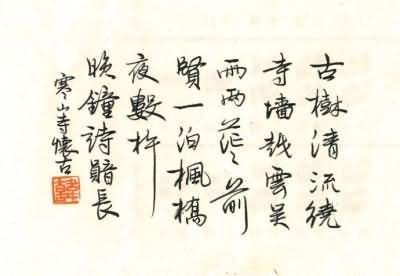作者或出處:司馬遷
古文《太史公自序》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公自序》現代文全文翻譯:
太史公說:「先人有過這樣的話:『從周公死後五百年而誕生了孔子,孔子死後至今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而訂正《易傳》,續寫《春秋》,探求《詩》,《書》、《禮》、《樂》之間的淵源呢?』他的意思是完成這一事業當在此時嗎?當在此時嗎?我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當初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政治衰落廢弛,孔子做魯國的司寇,諸侯陷害他,大夫們掩蔽他的賢能。孔子知道他的話不被人採納,政治主張無法推行,便通過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的大事,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標準,譏評天子,斥責諸侯,聲討大夫,以此來通達和闡明王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將我的褒貶態度作為空話而記載下來,不如表現在具體事件中更為深刻切理,鮮明曉暢。』《春秋》,上則闡明三王的道理,下則分辨人世各種事體的準則。辨別疑惑難明的事物,弄清是非的界限,確定猶豫不決的問題,表揚良善,批評邪惡,尊重賢才,鄙薄不肖,恢復已經滅亡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的世系,補救弊端,振興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內容。《易》是顯示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所以長於變化;《禮》是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所以長於引導人們的行為;《書》是記載先王事跡的,所以長於指導政事;《詩》記述山川、豁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長於教化;《樂》是音樂的依據,所以長於調和人們性情;《春秋》明辯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禮》用來節制人們言行,《樂》用來激發和樂的情感,《書》是用來指導政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說明變化,《春秋》用來解釋義理。撥正亂世,使它歸於正軌,沒有比《春秋》更為切近了。《春秋》的文字有幾萬,所要說明的意旨有幾千條,萬物的分離與聚合,都在《春秋》裡面。《春秋》之中,記載臣下殺死君主的有三十六起,國家被消滅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出奔逃而不能保住自己封國的不計其數。考察他們之所以這樣的原委,都是因為丟掉了根本啊。」
「所以《易》說『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因此說,『臣子殺國君,兒子殺父親,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它的由來是很久遠的了。』所以,享有國土的君王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則,前有讒臣卻不見,後有國賊而不知。作人臣的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則,做了正當的事卻不知道是否合適,遇到變故又不懂得變通。作國君或作父親的如果不通曉《春秋》的要義,一定會蒙受首惡的名聲;作臣予或作兒子的如果不通曉《春秋》的要義,一定會陷入到篡位、弒父的法網中而落得該死的罪名。他們的本心都還以為是在按規矩辦好事的,只是做了以後並不懂得其中真正的義理,受到憑空加給的流言蜚語而不敢辯駁。不通曉禮義的要旨,就會出現做國君的不像個國君,當臣子的不像個臣子,作父親的不像個父親,為兒子的不像個兒子。做閏君的不像國君,就會被侵犯;當臣子的不像個臣子,就會獲罪被殺;作父親的不像個父親,就沒有道德倫理;為兒於的不像個兒子,就會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過失啊。以天下最大的過失加在他們身上,當然只好接受而不敢抗辭。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根本法則!禮,在壞事發生前就加以禁止,法,在壞事發生後才加以施行;法的作用是比較容易看見的,而禮對人們的約束作用卻難於被人們所理解。」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候,上沒有聖明的君主,下不被信用,所以寫作《春秋》,留傳空文來評斷禮義,當作帝王的大法。現在,先生您上逢聖明天子,下有官守職位,萬事都已具備,各自按著適當的程序進行,先生,您所論述的,是為了說明什麼道理呢?」
太史公說:「哦,哦,不,不,不是這樣。我從先父那兒聽說過:『伏羲氏是最為純樸厚道的,作了《易》的八卦。堯、舜二帝的盛德,《尚書》記載下來,禮、樂也就興起了。湯、武時代的興隆,詩人歌頌它。《春秋》表彰善事,貶斥邪惡,推崇三代的德政,褒揚周王朝,並不只是諷刺譏笑而已。』漢朝建立以來,到了當今聖明天子在位,得到了上天的祥瑞,到泰山舉行過封禪大典,更改了正朔曆法,變換了車馬服色,承受天命,德澤無窮無盡,海外不同風俗的國家,經過重複翻譯,叩開關門請求貢獻物品和朝見的,說也說不完。臣下百官極力稱誦聖主的明德,仍然不能盡情表達自己的心情。況且,士人中的賢能者不被信用,那是國君的恥辱,人主明聖,但德行得不到宣揚,這是官吏們的過失啊。而且,我曾經職掌太史令之官,如果廢棄英明、聖智、盛德而不予記載,磨滅功臣、貴族、賢大夫的業績而不予敘述,丟棄先父所告誡的話,這樣,罪過就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只是整理、統一他們的世系傳記,並不是所謂創作,而您將這件事同孔子作《春秋》相比,未免言之差矣!」
於是我評論編次了這些文章。經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禍患,被拘禁在監牢之中。於是喟然長歎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遭到摧殘,再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又轉而深思:《詩》、《書》辭意隱曲,文字簡約,是想表達作者內心的思考的。從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於是演繹了《周易》;孔子被困於陳、蔡,於是寫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述了《離騷》;左丘眼睛失明,才寫了《國語》;孫臏被剔去膝蓋骨,就研究兵法;呂不韋被放逐到蜀地,世上流傳他的《呂氏春秋》;韓非被關在秦國的牢裡,著述《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賢人聖人感情憤發而寫作的。這說明,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鬱積,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所以追記往事,思念未來。於是我從黃帝開始直到漢武帝獵獲白麟的時候為止,敘述了陶唐以來的史事。